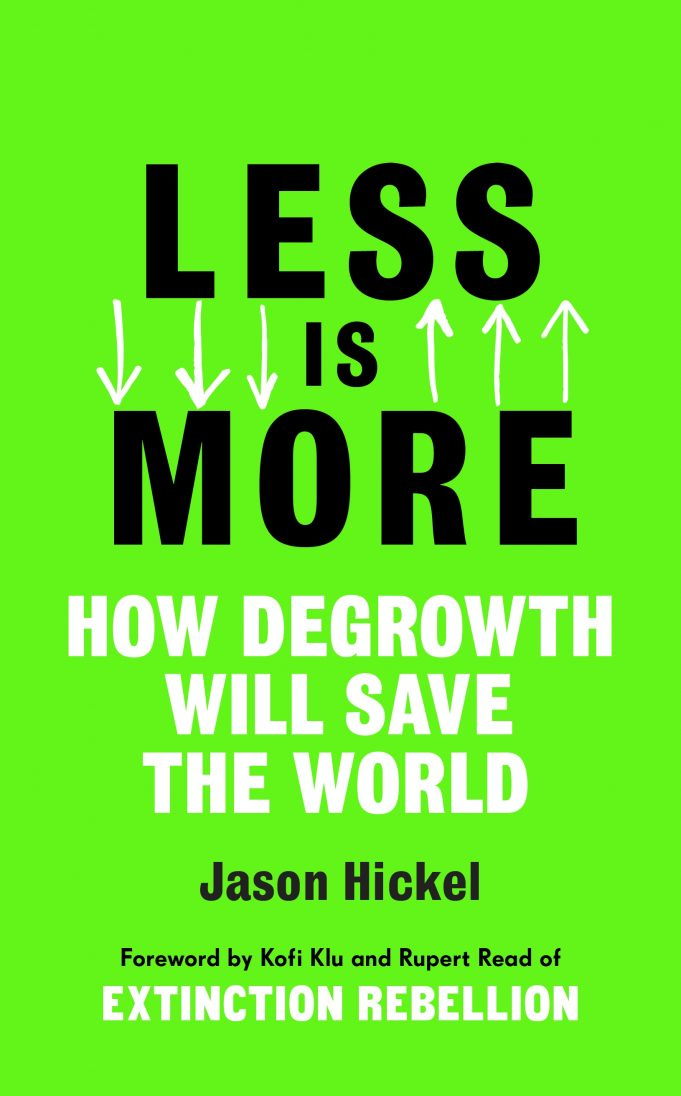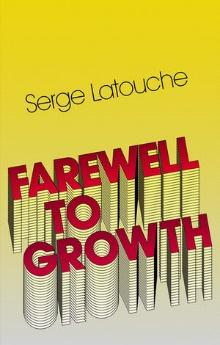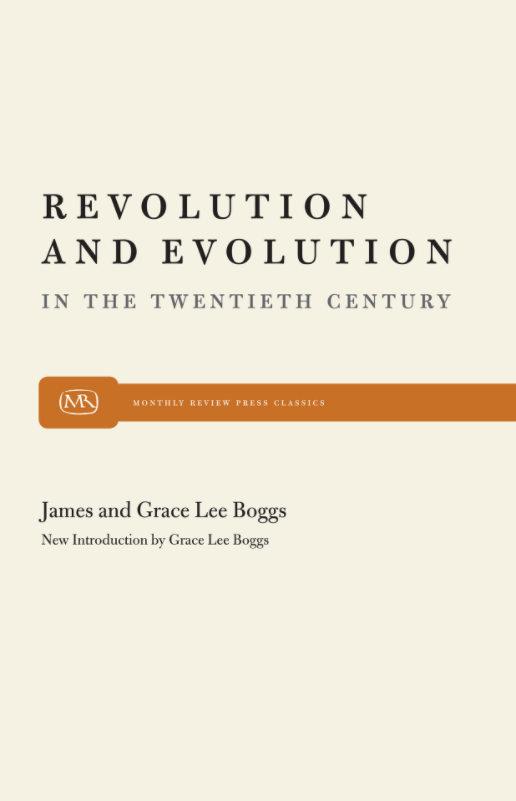“去增长”将如何挽救世界?第三世界不为西方背锅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2-03-18 阅读:1985 次
导 语
当今世界不平等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使用了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的地球生态资源。这样一个大的生态负担,依仗全球不平等的分工和贸易体系,透支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成本,滋养西方社会的高消费生活,不仅损害了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让地球生态难以持久。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不能简单的谈不要增长,因为第三世界仍然需要增长,而是要针对所谓发达国家(北方国家)的增长和消费开刀。而这又不是简单的中产阶级式(柴静式)的消费者自省,而是要对整个国内国际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这种变革无疑是有难度的。首先表现在,对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来说,社会变革不会带来消费和生活物资的绝对增加,而是要绝对减少,这样的变革可能吗?会受到欢迎吗?创作这篇文章的纽约去增长组织就做出了了不起的工作,值得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去了解。
作者|Jamie Tyberg 、Erica Jung (Nodutdal 组织的成员和纽约去增长的联合创始人)
翻译 | 于同、丁卯、Alvin
校对 | 侯牛
责编|守拙 侯寅
后台编辑|童话
1、引言:“去增长”,一个革命性的过程
“去增长”是一项针对全球北方的纠正方案,其纠正对象为“在国家与国际范围内,私人或政府单位建立并运营的增长驱动型对外发展项目”。由于核心经济以加速增长为使命,受此驱动,全球北方建立了一干机构:美国军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华尔街私人银行……以此来打破资源分配的平衡,以利于全球北方的财富积累。这样一来,全球北方经济的野蛮增长就扼制了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革命知识分子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和格雷斯·李·博格斯(Graces Lee Boggs)等人就将“去增长”概括为一种生态性补偿。他们坚称“在美国将要进行的这场革命中,人民不会获得物质财富,反而要做出物质牺牲,这将成为革命史上的首例”,因为“这个国家曾经谋取的物质财富,使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陷入了贫穷、落后、疾病和短寿的境地。” 全球北方的物质过度发展与全球南方的过度剥削之间存在矛盾。这表明,要使南方摆脱剥削,就必须先终结北方的过度发展。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正是剥削、侵占和积累体系的扩张撑起了社会开支,即社会剩余的分配方式。美国的物质过剩本应带来自由和平等,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进而能够把时间投入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中去。然而事实却相反,在强制性的资本主义环境下,普通美国人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哪怕最贫穷的阶层人口也会被资本主义吸引,不断地买,买,买”,同时却没有机会了解他们的社会责任或提高政治意识。这是“一种亟待纠正的反常现象”。基于这样的认识,“去增长”呼吁限制这种经济体的扩张,并设想了一种社会开支制度,既能创建共同意义,又能节省时间和空间,以推动社会责任与政治意识的进步。
最重要的是,无限的增长只属于少数人,而受此推动的社会开支制度延迟了我们人类整体的发展。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的革命家阿米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称之为“通过暴力篡夺来否定被统治者实现进步的历史过程”。于是,革命“在对抗现有制度的同时,又实现了更具人性的哲学飞跃。”然而,当下的我们正全速前进在毁灭物种与栖息地的道路上。
不过,在去增长运动的旗帜下,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条革命的道路。许多人选择了预演性政治模式,如合作社、社区花园和公社,这些虽然补充了革命目标,却无法胜任阶级斗争或其后的政治过程。于是,许多“去增长”的著作受到了批评。非殖民研究者帕丁·尼马尔(Padini Nirmal)和黛安娜·罗切洛(Dianne Rocheleau)在论文《在后发展的融合中实现非殖民化的去增长》中写道,虽然目前“去增长”的论述“在生态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它“尚且不能瓦解暴力、债务和死亡。”政治生态学家克莱尔·奥马尼克(Claire O'Manique)也认为,“虽然‘去增长’对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仅此还不够,”因为“任何旨在实现‘去增长’的运动都需要转变权力关系”。
关注“去增长”的杰出学者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曾发表著作《少即多:去增长将如何挽救世界》,2021年六月,钦奈研究员萨拉·亚伯拉罕(Sara Abraham)在对该著作的评论中指出,希克尔忽略了一点,即“如何与多方力量博弈并保持平衡,这才是政府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时所要考虑的”。另有两位研究“去增长”的重要学者文森特·列吉(Vincent Liegey)和安妮特拉·纳尔逊(Anitra Nelson),著有《认识“去增长”:一部批判指南》,他们认为,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领导的布加纳法索革命最终失败,是由于某些“独裁”策略,却忽略了桑卡拉遭到暗杀的背后有着更大的新殖民主义背景。一些观点认为,不采取革命行动就可以通过“去增长”实现社会整体的重组。这无异于重蹈历史错误,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贝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所说:“将一对矛盾的两个部分彼此割裂了,又将矛盾的两个部分与产生这对矛盾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相割裂了。”
经过我们的分析,要实现“去增长”,就得“推翻一切现有的财产关系,并摧毁一切直接或间接拥护现有财产关系的机构”。环境研究员韦伯伦·J·本斯特拉(Weibren J. Boonstra)和索菲·乔斯(Sofie Joosse)赞同这项分析,他们写道:“我们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实现‘去增长’,因为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只要生产资料中还存在私有财产,去增长运动所倡导的“由自发组织的决策过程在内部构建”的生态社区等各种方案就无法持续运行。而只要我们准备好为革命履行职能,“去增长”就能够实现。本质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
本文献给全球北方的承诺者——“去增长”不是空话,而是一个严肃而真诚的愿望。
2003年2月15日,在纽约市举行的反战示威中,抗议者们手持充气地球。数万人参加了这次集会,响应世界各地的和平示威活动。
2、废除增长-工业复合体(简称增工复合体)
有史以来,经济增长的过程就不乏暴力。今天,美国仍在利用奴隶制的遗产--通过剥削监狱劳工以取得显著的发展并扩张其霸权。经济增长与奴隶劳力两者是紧密勾连的,这就要求去增长运动审视大规模监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然而,针对监狱的去增长分析却屈指可数。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加利福利亚州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大规模监禁情况,以及增工复合体中的垄断金融资本的流动,来揭示这一腐败链条。最后,我们希望去增长运动能够增加一个主要目标,即加入监狱废除主义者的行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时代到来,美国也巩固了其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独特地位。因此,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投资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军工复合体,主要依靠大量的国防部(DOD)合同来增加联邦投资并推动其经济增长。然而,由于长达20年的越南战争造成了联邦赤字,美国大幅削减了军费开支,这使得加州的失业率激增至11.1%,高于当时的全国失业率。因此,监狱被提议作为解决中央山谷地区经济停滞或萎缩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从1982年到2000年,加州的监狱人口增长了500%。追溯到1983年,这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建造计划",该计划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一种能转移公众对政府主导的经济不平等注意力的有效方式,以及一个能剥削剩余劳动力和可利用土地的手段。之前在加州的国王县,“当地官员用未来20多年的烟草结算款,从债券市场上换取了1800万美金,建造了一座新监狱,而这些结算款本应该用于当地的医疗保健”。中央谷地的农村地区,如阿韦纳尔,还特别请求允许在当地建造监狱,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如今,加州的一些监狱是作为电子垃圾回收站在运作。例如,在加州阿特沃特的美国监狱,占据了前卡斯尔空军基地的一部分,该基地 “被用于运营和维护国防飞机的燃料、油、溶剂、清洁剂和油漆所污染”,因此,被监禁的工人们其实经营着联邦监狱工业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站之一。每天,他们都暴露在有毒金属中,这些金属是在处理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机中的阴极射线管时产生的。在这种前提下,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不可能是公正的。
这并不是一个反对可再生能源的论点;相反,这是一个在考虑到生态极限以及全球种族平等的前提下,如何生产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论点。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描述前殖民地国家“被动地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客观要求”时,称他们“采纳”,或者“使用了类似资本主义的方法”。尽管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前殖民地国家仍受制于“殖民国家通过其巨大的胁迫资源”所制造的困境。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也与这种处于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
什么是垄断金融资本?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描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得到了充分的巩固,特别是在美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其结果是少数巨头公司控制了大多数行业。”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美国的垄断地位稳如磐石。”1980年至2008年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从15000家倍增到82000家,并成为 “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排名前147位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近40%的经济价值,并且它们的控制力还在持续增长。
此外,这种公司权力的集聚有助于 “维持美元作为世界法定货币的地位,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积累要素”,这使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特殊的优势。通过构建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秩序,使得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和所有外汇交易的88%,美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穷国补贴富国的世界体系。在本国政府为帝国主义所裹挟,以及国际移民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第三世界经济体的工人们被迫为帝国主义企业和金融利益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全球北方的核心经济体则“主导着世界经济的主要部门”。
在研究21世纪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的转变时,中国经济学家程恩富和鲁保林哀叹道:“跨国公司都是有组织的实体,而全球的劳动力却极难有效地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我们的进攻必须包括我们对其他人的组织。去增长运动的组织者必须坚持废除增工复合体的目标,这个复合体是由监狱和垄断金融资本结构组成的,它们支配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组织——这是集体斗争、集体学习,以及建立一个去增长的世界的先决条件。
3、告别自由散漫,走向团结组织
“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组织。组织是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这三个概念是相互必要的。你不能只有理论和实践,必须要有一个组织。”
——维杰·普拉萨 (Vijay Prashad)
去增长知识分子泽格·拉图什(Serge Latouche)在他的《告别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八个相互依存的去增长原则。它们是:
1、重新评估我们的工作重心;
2、重新思考财富、贫困、价值、匮乏与富有等等关键概念的定义;
3、重构生产组织和社会关系,以适应新价值;
4、在南北国家之间,在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和个体之间开展对财富和自然资源获取的重新分配;
5、将储蓄、融资、生产和消费再本土化;
6、削减生产和消费,尤其是使用价值不大却对环境影响巨大的商品和服务;
7、产品的重复利用;
8、以及循环利用废弃物。
此外,政治经济学家休伯特·布赫-汉森(Hubert Buch-Hansen)概述了“社会经济范式转变的四个先决条件:深层危机、一个替代性的政治计划、一个由广泛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并在政治斗争中推进该计划,以及广泛的共识。”泽格与休伯特的主张都共同蕴含着一个协同行动计划,其目的在于改变结构、转变范式,并动员人们重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实现这一切的第一步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去增长)组织。倘若我们连组建这样一个去增长的组织都做不到,又如何能指望建设一个去增长的城市、国家和世界呢?
通过组织,我们“能够不断对自身的理论和实践重新评估,能够不断改造我们自己,以便更好地胜任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詹姆斯·博格斯和格蕾丝·李·博格斯(Grace Lee Boggs )写道,我们“对于那些有志于服务集体而走到一起的人,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改造,向他们灌输一种发展和维系集体认同和共同目标的强烈意识。在初始阶段,去增长组织应该专注于内部建设。倘若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在不断实践中对理论的更新,组织会更易受错误的去增长路线的影响。”
在纽约去增长组织(一个由纽约市倡导去增长的有色人种所组建的团体,以下简称纽约去增长)的第一次会议上,所有与会者分享了他们参与组织的能力,对去增长组织不同层次的理解,以及对构建这一新生组织的思考和希望。那次谈话决定了开头几个月内部政治教育的课程内容。
在初创阶段,去增长组织应该设立自己的统一原则,这不仅有助于识别组织反对什么,也有助于明确组织支持什么。这样一个统一原则可以看起来像是一份要点列表,一个使命声明,一组指导性问题,但总而言之它们应该存在,这既是为了确保所有组织成员对彼此负责,也是为了保障组织的工作服务于成员的共同价值。这样一份文件的意义在于为组织锚定意识形态,使我们可以仔细纠正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源自于“资本主义数百年的稳定集中”,或是源自“在某些地区存续了数千年的等级制度”。在纽约去增长中,我们第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内部政治教育,然后以集体参与的方式起草组织的使命声明。这份声明写道:
纽约去增长是一个由有色人种所组成的团体,组织设于Lenapehoking[1],我们认为去增长是一种生态补偿形式。我们以关爱、充足和自主的原则来团结组织成员和确立工作重心,旨在挑战和祛除无限增长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开发资源和举办教育活动,我们为活动者和组织者赋权,使它们在组织和活动中践行去增长的价值和实践。
写这份声明要求组织成员在集体的存在目的上,在现有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地位上,达成意识形态同一。如果没有初期对组织内部建设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统一的原则必须能够随时接受修订,允许组织评估其进展、成功和失败,并由此相应地调整其运动。在制定这些行为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实践了关爱自己和他人的原则,并将建设生态限制社区的思想付诸行动。正确的思想来自实践——当我们以集体的形式推进去增长时,要在前进的过程中纠正方法,自主构建去增长的世界。“我们是为了满足集体需求而非个人需求而工作吗?” 我们的工作是否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广泛的资源榨取的?对于诸如这样的问题,在工作的各个阶段,也无论工作内容是什么或涉及到谁,我们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去增长组织还必须学会关注差异性,认识到每一个成员所具备的能力、构想的计划,甚至与组织其他成员的互动模式都是不同的。正如革命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权利平等以相同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权利平等以不平等为前提的。”“而去增长组织必须将权利的概念转变为角色的概念,不同人基于他们的能力、年龄、经验等,在一个组织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朝着一个统一的目标努力。”也许一个组织最易达成的特征就是它的流动性和未定型的特质——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受欢迎的,因为(去增长的)工作是持续的和共有的。以投身革命性变革为共识而共同努力,我们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我们所能作出的贡献,而且我们坚信这项工作将始终走下去。
詹姆斯·博格斯和格蕾丝·李·博格斯还指出,“在招募成员这一方面,组织应该极其谨慎地对成员进行筛选,将目标放在缓慢而质变的增长,而不是快速扩张,要避免一种判定组织成长的方法,即根据成员数量而不是根据他们对组织的意识形态和发展计划的忠诚和投入来判定。”组织的发展需要时间和耐心,构建一个去增长的世界也是如此。“当我们审视一个团体的革命内容时,如果是以它怎样的激进好斗,或是以它如何从厌倦和挫败中获取兴奋和慰藉的视角出发来审视”,那么我们就抽去了这个团体“集体斗争的发展”的内容。
“去增长组织必须努力构建一些日常程序,包括定期的会议和明确的分工,使成员充分意识到该组织推动人类进步的责任。”例如,纽约去增长每隔一周聚会一次,成员们定期分享额外的集体活动机会,这些活动涵盖教育课程、令迁出辩护、社区计划、参加集会以及在本地公共空间中的相互陪伴。在一个组织中,我们将忠诚与关爱的意义内化。通过在组织中参与学习,我们让去增长的立场和行动成为我们无意识的一部分。
此外,去增长组织最终应该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方法,使得集体自我限制,作为去增长原则中固有的自治原则,得以实践,在这样的实践中,“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福祉而限制我们在非人类世界的足迹”。在《二十世纪的革命与进化》(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詹姆斯·博格斯和格蕾丝·李·博格斯解释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革命组织中的重要性:
首先,(通过所有相关者最彻底的讨论和准备)以避免错误的必要性;
第二,认识、承认和纠正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的必要性;
第三,明确错误责任的必要性。
做这些不是为了把责任推到个人身上,而是为了使个人和其他人能够从错误中吸取适当的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去增长组织应该维持一个辩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其成员参与行动能够为组织的计划和实践指明方向,反之亦然。无论我们在哪,如果要朝着去增长的方向前进就要在融入一个实践去增长价值并在社区中推进去增长理想的组织中。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错误是必然会发生的,但从事革命工作首先就要相信人们有能力改变,认识和纠正这些错误,并最终防止这些错误。去增长将是“群众文化革命所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会逐渐适应和养成去增长的习惯,并为后代将去增长的价值制度化,直到我们不再需要去增长。
生态研究员马克斯·艾藻尔(Max Ajl)在他2018年的文章《思考去增长》(Degrowth Considered)中警告说,“去增长对于(生产)闲置的用力可能不能太过火,”因为“一旦生产本地化,贫穷国家将着力于养活自己,而富裕国家无法再用化学产品替代(本土)知识、注意力和劳动力,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所需要的劳动或维持农场的劳动将比去增长所预期得要更多。”
当我们必须推进农业集体化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一领域是由三家跨国公司——杜邦、孟山都和先正达——所把持的。这三家公司控制着全球55%的种子市场,而为养活世界上所有人而进行农业集体化的任务将需要我们的劳动。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项任务都需要我们的劳动,而共同劳动的分工和构建去增长世界的分工都需要组织的存在。投身去增长永远不会太晚。
注释:
[1] 十六十七世纪北美印第安人德拉瓦族部落的所在地,原住民后遭欧洲殖民者驱逐,疆域大致从美国康州西部到特拉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