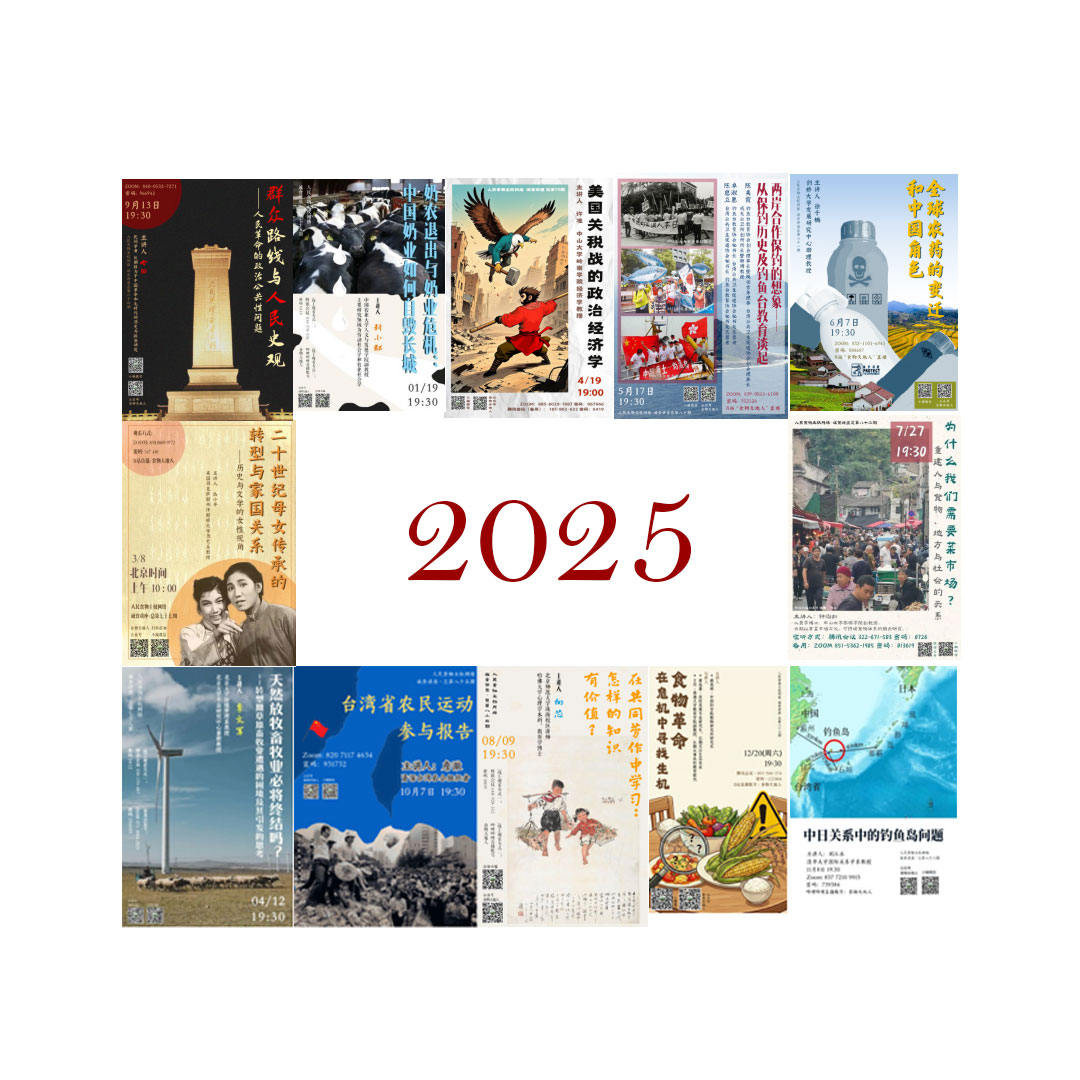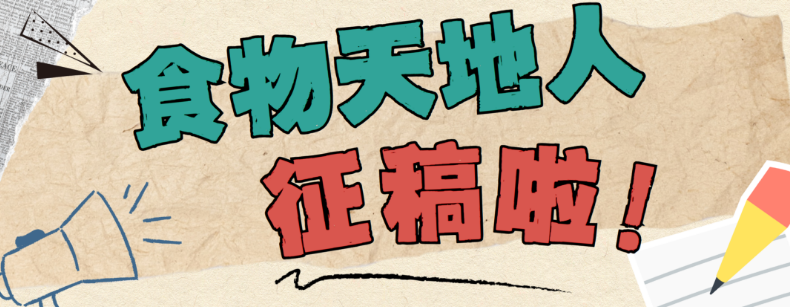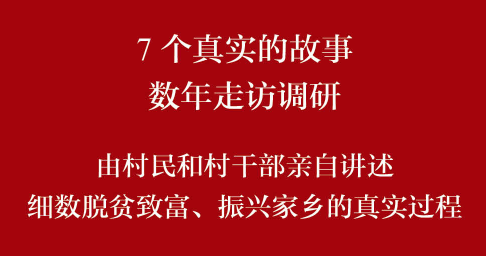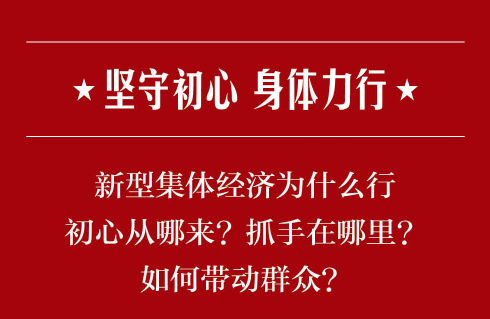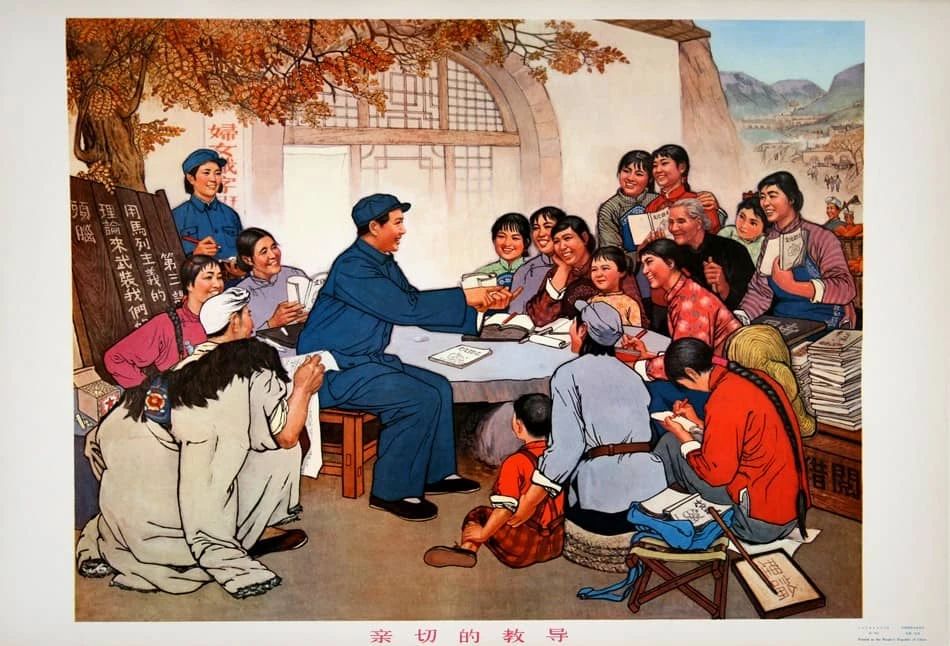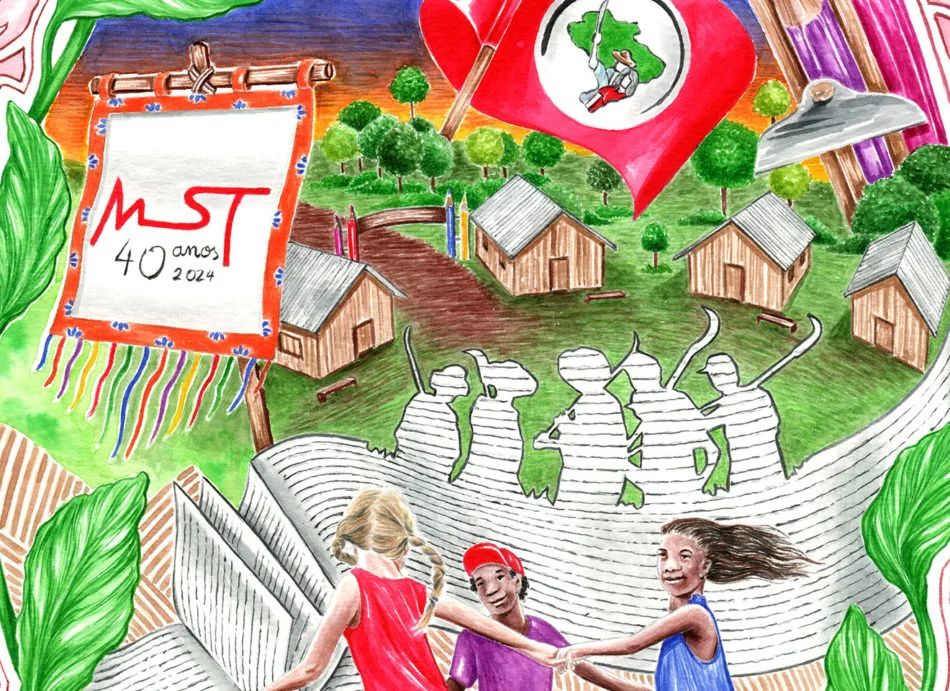【原创】面对阶级分化,“社区营造”还能走多远?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5-07-03 阅读:3686 次
食物主权按:遗憾的是,国内学习台湾社区营造,抽离了其社会运动的内核,刻意回避阶级问题,不去试图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结构,而是采取文化建构的路径,试图通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消弭社区成员之间的隔阂。这种取巧的做法,也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注定不能带来根本的改变。
最近这些年,社区营造的概念在大陆迅速升温,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人们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沿海地区,社区营造这一新生事物备受推崇,政府和学术界的一些人都热衷于谈论社区营造的理念和理论,推动社区营造的实践。
所谓社区营造,就是指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通过广泛参与的集体行动,共同解决社区面临的问题,改善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创造共同的福祉,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亲密友善,社区更有凝聚力。总之,这是一种以居民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社区改良运动。
社区营造之所以在大陆能够迅速火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建设陷入困境。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集中爆发,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为了应对这些矛盾和风险,党和政府先后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社会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努力缩小“三大差距”(工农、城乡、贫富),促进社会和谐。这种初衷是好的,然而,在现有的科层体制下,各级政府只是对上负责,把社会建设作为一项行政任务,为了应付上级考核,为了做出政绩,每个部门都忙得团团转,热衷于短平快的项目运作,集中资源打造样板,追求媒体宣传效果,绝大多数项目都沦为形式主义、形象工程,花钱很多,效果很差,老百姓受益很少,一些官员和商人却从中渔利,被老百姓批评为劳民伤财、瞎折腾。其实,政府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居民广泛参与的社会建设,既没有效率,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希望通过社区营造这种方式,让老百姓自己动起来,使自下而上的力量与自上而下的力量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村民的自治。
2、台湾地区社区营造成功经验的典型示范效应。这些年,大陆赴台湾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去过台湾的人或许并不羡慕台湾的工业和城市,却无不被台湾的农村和农业所折服。过去三十多年,大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大跃进,城市越来越光鲜亮丽,农村却越来越衰败,资源流失,环境破坏,人际关系淡漠,农村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新都市人无法触摸的乡愁。相比之下,台湾地区在实现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农村社区也充满生机和活力,乡土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例如桃米社区的青蛙王国,打动了无数人。台湾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在大陆知识界广泛传播,对大陆学者、官员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3、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热情推动。热衷于社区营造的大陆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厌倦了枯燥乏味、人情冷漠的城市生活,渴望返璞归真,回到半耕半读、天人合一的田园生活,乡村成为梦想中的桃花源。这些人推动的社区营造,其实是在别人的地盘上营造自己的社区,并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营造。另一种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以乡建学派为代表,他们忧国忧民,又具有乡土情怀,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现代化带来的乡村凋敝,走出危机的出路是重建乡村社会的主体性。他们继承梁漱溟、晏阳初等民国乡建学者的道路,身体力行地推动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希望农民能够早日觉醒,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园。
活跃的精英与沉默的大多数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人参与、当家做主”,社区营造倡导的这些理念看起来很美,在实践中能够真正落实吗?2013年至今,珠三角某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学习台湾经验,在F社区启动了一场本土社区营造的试验。作为高校研究人员,我有幸深度参与了这一场社会实验,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切身体会。
F村地处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历史上一直有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村里有些家庭通过经商、开办工厂、承包鱼塘等方式积累了财富。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村里随处可见的豪车、洋房,展示着这部分人的经济实力。
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分化机制意味着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除了少数的精英,F村绝大多数村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F村不是大规模的工业区,村里外来人口不多,村民没有出租房屋的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厂房出租和鱼塘发包,村民每人每年从集体经济获得的分红,多的千余元,低的只有几百元,属于聊胜于无的状况。村里年轻人,和内地年轻人一样,以进厂打工为生。这些年,村里年轻人陆陆续续搬去城镇居住,留守在村里的多是一些中老年人。村子周边的工厂更喜欢使用年轻劳动力,这些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守着工厂,却无法进去工作。他们既无能力承包鱼塘,也没有经商的资本和头脑,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以外,虽然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却没有就业机会,只能从事环卫、服务员、商贩等低端服务业。
F社区的阶层分化,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村民的分化不仅体现在财富的拥有上,还体现在生产关系上。村里一部分人开工厂,雇佣另一部分村民当工人;村里一部分人承包了游船业务,雇佣另一部分人帮忙划船;村里一部分人开餐馆,雇佣另一部分人做厨师和服务员;村里一部分人承包了鱼塘,雇佣另一部分人帮忙打理。在这个熟人社区,人与人之间存在血缘、血亲缘、业缘、地缘等多重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给阶级关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传统道德伦理对雇主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使之碍于情面,不能采用过于粗暴的管理方式,但是,主雇双方都清楚各自身份,老板终归是老板,打工的终归是打工的,在谁说了算的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这样一个阶级分化的社区,虽然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社区的主人,但是,不同阶层/阶级的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和程度在实质上是不同的。
先富起来的精英阶层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见识让他们在公共场合很有底气。他们是新时代的乡绅阶层,活跃在社区公共舞台。政府非常注重依靠这部分精英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社区有影响力,也因为他们为人精明,头脑灵活,能很快地理解政府的意图。通过与这一部分人合作,政府的一些行政意图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而这些精英阶层也依靠行政力量来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
相比之下,底层群众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底层沉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公共事务了解不够。珠三角的基层政府一直在推动村务公开规范化,村里各种重大信息都能做到按月公布,但村里的中老年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很难理解那一堆的数字表格,还有各种会计报表、专业术语。二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政府推动社区公共治理走向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这也意味着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门槛提高了,作为最基本的要求,参与者必须能够用一套与时俱进的、规范化的语言,简明、准确、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底层群众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三是底层群众的意见不被重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社区虽小,也是一个利益争夺的场域,精英阶层掌握话语权,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影响公共决策,贯彻自己的意图,而底层群众虽然人数众多,却没有组织,处在弱势地位。底层村民并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说话没有分量,说了也没用,自然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F社区的社区营造,组织动员了一些底层群众,做了一些小型的社区改良项目,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底层动员。
社区营造,能走多远?
当前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部分政府官员,之所以热衷于推动社区营造,都是不满于现有的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又不认同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方案,因此选择第三条道路,想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背景下挽救日益衰落的乡村,重建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然而,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断加剧社区成员的分化,高度分化的社会成员,还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吗?在这种背景下,社区营造究竟能够走多远?
从F社区的案例可以看出,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社会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基本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穷人与富人,当老板的与打工的,彼此的身份边界已经非常清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品味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很多事情上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文化共同体也产生裂痕。最终,富人陆陆续续搬出传统社区,在地理空间上与穷人区隔开来。
在一个阶级/阶层分化的社区,社区成员名义上是平等的,人人享有有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但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政治平等和民主参与只能是一句空话。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底层的利益诉求被压制,底层无法发声。如果不去挑战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结构,不让底层彻底翻身,重塑底层的主体性,就不可能真正把底层民众动员起来。而要彻底改变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结构,斗争和冲突不可避免。正如台湾学者夏铸九教授所说的,社区营造的本质是社区培力和维权。事实上,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一些成功案例,恰恰是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一起,与资本和权力进行抗争,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底层的团结,而后才有一系列的家乡再造项目。例如台湾著名的美浓社区,其社区营造恰恰发源于本地居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建设水库的社会运动。
遗憾的是,国内学习台湾社区营造,抽离了其社会运动的内核,刻意回避阶级问题,不去试图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结构,而是采取文化建构的路径,试图通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消弭社区成员之间的隔阂。这种取巧的做法,也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注定不能带来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