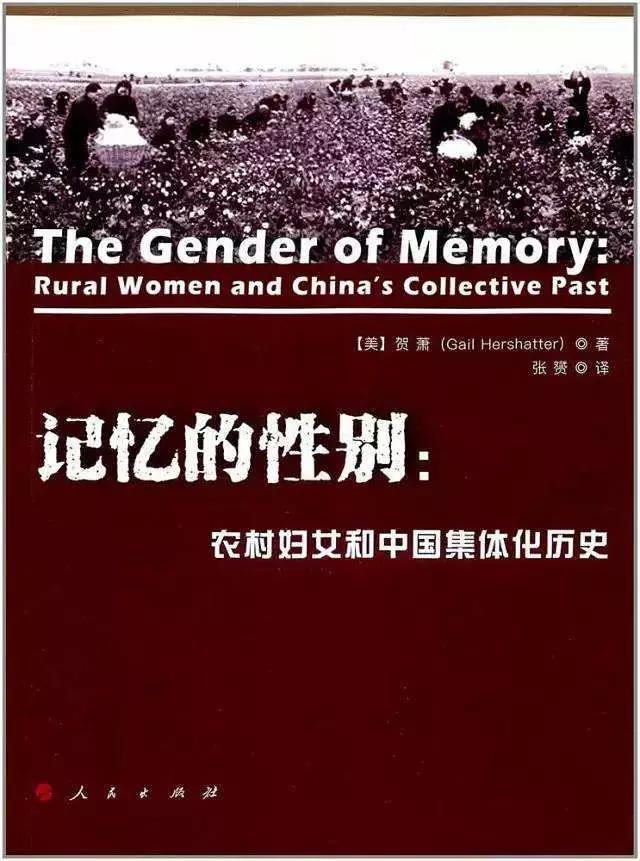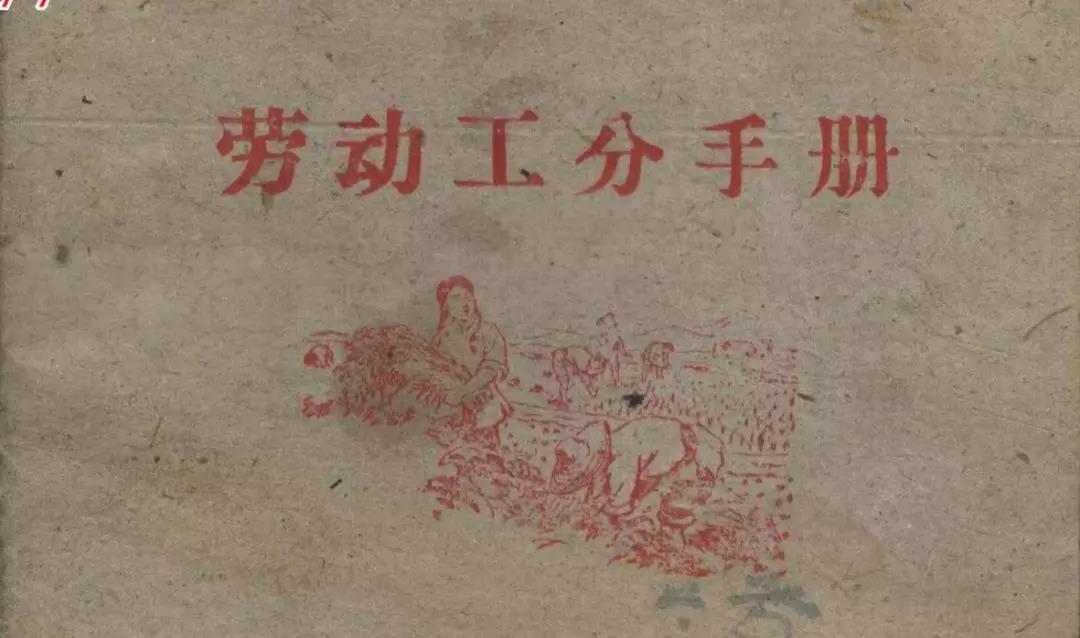贺萧: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妇女
来源: “一颗土逗”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8-10-06 阅读:3841 次
食物主权按: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的书评中,学者刘亚认为作者通过地方性、性别、家庭等不同的维度,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超越了以往大多数关于集体化妇女研究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展示了妇女的生命轨迹与农村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让读者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并展开对于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想象。让我们阅读刘亚的书评,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性别》,走进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妇女们。
贺萧的恢弘巨作《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历经十年、根据七十二位农村妇女的访谈以及大量细致的档案材料整理而成的口述史距其英文版的出版有整整五年,这样的等待,对于那些迫切地想要了解毛时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如何进入地方社会、带来哪些地方政治与经济景观的变迁、以及农民(妇女)又如何理解与回应这些变迁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值得的。正如香港大学《中国评论》编辑路易斯·爱德华在评论时说,这本书“在未来几十年都将会被阅读,且毫无疑问将鞭策其他人去开展新的、激动人心的、有关其他时段、中国其他偏僻农村的研究。”
中文版《记忆的性别》 来源:百度图片
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
建国以后,共产党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方案:婚姻家庭变革、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短短的时间画卷上,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共产党立志摧毁封建的、官僚的资本主义旧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雄图大略。然而,“大跃进”失败带来的沮丧在整个乡村社会弥漫,成为共产党政权在不少重大议题上进一步探索的主要障碍。相较于1950年代各种运动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中国农村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可以说是过于静默了。
一直以来,学界与社会对于中国在1950年代乃至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充满了好奇。官方的记载和讨论主要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每一项改革方案以运动的形式发起,接着是一系列的宣传部署、问题修正,最后是运动废止。整个过程往往在档案里会有明确的呈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雄心的政权,如何让农民理解其改革方案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面临的课题。然而,地方民众如何理解运动,如何迎合,如何抗拒,如何将各种新观念整合进自己的日常实践,地方政权又是在哪些力量的合力下达成平衡——这一切在官方的叙事里却是不清晰的。
另一方面,学界对新政权的最初十年也有极大兴趣,但学术研究的焦点往往放在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而非农村。虽然少数学者,如韩丁、塞尔登,对于处于运动漩涡的农村进行了精细的描述,但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使得播撒其间的社会主义种子呈现出不同的生长过程和形态,而探索其间的差异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丰富内涵的重要途径,也更能有效地回应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质疑与曲解。
贺萧在书里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地方性问题。“即使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颁布的最具指示性的法令,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被贯彻实施,由当地干部根据特定情境对法令作出阐释、修订、强调以及改变。无论在何处,国家政策的实施都取决于地理环境、事先的社会安排及当地的具体特色”。透过这样的视角,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地方传统背景之下国家话语的矛盾之处。比如,在官方叙事里,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看作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然而在贺萧考察的位于陕西省的四个村庄(分别位于四个县城),妇女们在解放以前从来都不是“幽居隔绝”。事实上,战争、匪盗、饥荒及疾病导致男人长期缺席,妇女从来都是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她们干农活以获得食物,纺织棉花卖布挣钱交税,只是在新国家的话语里,妇女早已出现在社会空间的事实被排除了。
这种“自下而上”的视野还显示,国家权力进入农村,对于旧“封建”思想并非采取全盘抛弃的策略,而是以一种矛盾的手法处理新政权在基层生根的问题。国家一方面批判这种阻碍妇女追求自由解放的封建礼教,另一方面却在塑造“新社会的理想新妇女”的过程中将妇女的传统美德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国家不再是抽象的地方社会的“侵入者”,妇女“作为国家美德化身的身份使‘国家’和‘社会’分界的产生成为一个地方性的议题,甚至延伸到家庭空间以内。国家成了一个邻居,甚至成了家庭中的一员”。贺萧对于地方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新的社会制度脱胎于旧的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国家的妥协,抑或策略,从而使得旧的社会规范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占领社会生活的制高点。这在妇女解放的议题上尤其明显。
学者贺萧 来源:百度图片
集体化:记忆的性别
《记忆的性别》一书里最令人着迷之处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农村妇女关于社会主义丰富的经验被记录下来。不同于主流男性叙事的视角,妇女们的讲述不仅使宣传画里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场景变得无比生动,那些被排除在画框之外的、可能曾经被认为不和谐、不知如何安放的细节,如今被关注,被仔细地整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一幅更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画卷。“妇女既是革命性变革的对象也是行动的主体”,社会主义历史的书写,若缺乏对半数人口经验的整理,尤其是她们在这场伟大变革中的角色、贡献,一定是不完整的。
尽管农村妇女从来都不曾有过“幽居隔绝”的生活,但出现在公共空间并不意味着她们在地方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将妇女从封建家庭中解放出来应该以妇女是否参与地方政治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从妇女经验来看,新社会带来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公共生活的建立和参与,但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正如同贺萧在书里描述的,妇女被国家塑造成集体的一分子,在地方重组中,妇女不仅仅是动员的首要对象,也往往是各种方案主要的执行者——从互助组、合作社带头人,到劳动模范直至公社党委书记。但地方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与妇女本就不熟悉的公共生活为变革带来重重障碍和阻力。不过,那些针对妇女进入公共生活的反对的声音,虽然在事实上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权力进入地方社会、重塑地方公共空间所遭遇的抵抗,但或许正是由于面对各种各样的冲突,妇女才开始思考她们是谁、在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个人觉醒才是迈向解放最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合作化运动的日益展开,农村妇女开始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劳动者。社会主义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通过对劳动价值的制度性肯定以及对劳动者的赞美,国家实现了劳动者生产的主体性并力图最终实现其社会的主体性。在妇女们的回忆里,建国后最初的几年是伴随着歌舞、说笑度过的。由于田野里的工作、数不清的晚间会议,同龄妇女尤其是未婚女子有了许多“被批准和认可的”碰面机会,劳动极大地扩展了妇女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进入高级合作社以后,集体劳动不仅成为妇女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作为社员的她们获取合法身份的唯一渠道。作为日常实践的“劳动”在重新塑造妇女生活经验、重新定义性别关系方面的影响深远。在这里,官方主流叙事里常常隐藏的那些有关性别的艰辛、困惑、挣扎甚至抗争的声音显得异常清晰。
贺萧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同工同酬的讨论上。自合作化运动以来,按工分计算收入的做法越来越普遍,然而工分制本身的复杂性却是新生的社会主义集体必须面临的挑战,在考虑劳动者体力上的差异、工种、工作的时段、工作地点的远近、劳动价值的计算方式(计件和计时)等因素的同时,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远非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干部还是普通劳动者都无法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往往选择容易操作但可能牺牲部分公正的策略,比如简单地按照男女的范畴确定工分标准。在贺萧的书里我们也看到,劳动的价值“不是由一天工作时间的长短或工作的任务来决定,而是由是什么样的人从事劳动来决定”,男子整体上获得比妇女多得多的工分。
劳动中的妇女 来源:百度图片
这种明显有悖于同工同酬原则的做法,正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共产党没有恪守承诺努力推动男女平等的表现之一,也是众多批评者将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吃大锅饭的主要证据。尽管贺萧对此也持批判的立场,不过她的研究也显示,国家并非对此袖手旁观,妇联在面对同工同酬和调和性别差异等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仍然努力维护妇女权益。而妇女的叙述则将我们引向同工同酬在实践过程中更丰富的面向。我们看到,由于农业劳动的特点,男女体力上的普遍差异的确在创造的劳动价值上有所体现,但同时,能力强的妇女仍然有机会通过有意识的斗争获得同工同酬,而这一点又常常与妇女生命周期的特点相联系。比如,上了一定年纪、有不少孩子需要照顾的妇女,无论是出工的天数还是能胜任的工作,往往少于年轻未婚或未生育的妇女,拿到手的工分自然就会少很多,而后者通过主动报名承担“重活”,与男子的工分相差无几。此外,合作社也采取计件的方式计算劳动价值,一定程度上地弥补了按性别评估工分可能有失公允的做法,虽然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记忆的性别》的另一个成就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遮蔽的历史世界”。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农业女性化的历史往往只追溯到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认为市场化改革将农村剩余男性劳动力带离农村,流向沿海城市,留下妇女以完成当时还未免去的各种税费任务。然而妇女们的回忆显示,随着社会主义“高潮”,男子被派去从事合作社里其他工分更高的劳动,比如照看机器或者副业生产,妇女成为常规的农业劳动力,开始全面承担此前主要由男子负责的各项农事活动,甚至连防涝这样的“重活”妇女也会参与其中。“妇女不出勤,庄稼靠谁做呢?”年轻的共和国在农业方面的成就,是妇女们作为核心劳动力所创造的,这段似乎没人留意的历史,若不是妇女们的讲述,恐怕将永远留在尘埃里。
在这个农事女性化的过程中,原本以性别作为区分范畴的“重活”与“轻活”,“技术活”与“非技术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尽管这消解了农业生产领域所谓身体“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但又埋下了在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隐患——之后的几十年里,国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对农村、农业的过度索取导致农村的普遍贫困,阻碍了农村妇女的经济发展;转型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过程中,妇女也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
家庭的变革:一场没有真正开始的革命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最后的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在家庭领域中位于主导地位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如何改造家庭、如何处理家务劳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否有决心、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妇女的标准。
婚姻法图解通俗本 来源:孔夫子网站
社会主义中国对家庭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婚姻法》的颁布开始的。在共产党与新近成立的中华妇女联合会看来,妇女地位低下,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家庭制度。因此,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必须以改造私人领域为前提。但是,改造私人领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大量文献显示,《婚姻法》的颁布在农村社会激起了普遍的反响。男性农民将之视为“离婚法”,基层干部不配合,伴随着这些消极的反应是各个地方不时发生的与婚姻相关的伤害妇女或妇女自杀的报告,而这也是不少西方女权主义学者批评共产党没有有效贯彻落实《婚姻法》的原因。然而,这些文献的问题是,除去数据和千篇一律的叙事,我们听不到妇女的声音——一场以解放妇女为主要目标的婚姻家庭改革运动,妇女的声音何以能缺失?她们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她们的生命轨迹是否且如何因社会主义运动而改变?
《记忆的性别》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妇女们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正如同暴力在婚姻改革运动中属于极端现象,抗争成功从而获得婚姻自主的个案也不多见。大部分妇女的生命依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前推进,国家效应被原有社会规范大大抵消。究其原因,按贺萧的分析,一方面,婚姻的缔结不仅仅涉及两情是否相悦,婚姻的物质基础对于多数妇女来说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考虑,然而“革命当时还未有开始触及物质条件的问题,没有任何蹲点干部或者革命良方能够解决她的困境”。另一方面,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事情,婚姻家庭中交缠错综的社会关系远不是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叙事能够涵盖的。贺萧因此提醒我们,在理解集体化时期的婚姻变革时,要关注“妇女在维系或者离开一段婚姻时,她们自己在感情、现实和政治之间作出的利益权衡。这些权衡有助于使她们成为具有美好品德的妇女,值得被颂扬,并易于被她们的社区辨识”。
一个许多人都好奇的问题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否曾经打算消灭家庭制度?从《记忆的性别》所呈现的看来,针对妇女的解放策略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私人生活。在生产领域,妇女依然是家庭生产和情感活动的主要承担者。随着集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国家在对于“劳动者”妇女不断提出新要求的同时,对于妇女家务劳动的负担(因家庭规模扩大而越发沉重)却保持沉默。贺萧因此将国家在私人领域改造方案的失败视为“理论上的忽视”。她认为,不同于帝国时期的思想家或者20世纪早期的活动家——前者将家庭看作是社会秩序和国家运作的基础,而后者则视家庭为公共恶习的根源——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政策将家庭描述成暗藏封建残余和阻碍社会主义的地方。
当然也有研究显示,国家并非一直对家务劳动“视而不见”,国家一度曾试图将家务劳动理论化以使其纳入社会主义生产的体系,只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家务劳动话语被革命话语所代替。或许这些研究对象不同、结论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研究正是“地方性社会主义”的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复杂、丰富的表征。但对于之前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对于家庭的态度问题,显然这些研究都无法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许,与其讨论共产党是否打算消灭家庭,不如看其有关家庭的改革方案是否实际上削弱了家庭的父权制基础。
贺萧花了大量的篇幅记录“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的“五化”实践:食堂化、缝纫化、产院化、托儿化、磨面加工化。主流的叙事往往将“五化”描述成国家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而不是妇女本身的策略,贺萧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窠臼,将对于“五化”的记录和讨论放在了题为“劳动者”的章节。然而,倘若我们将关注点放在改革方案本身,则会发现其对于家庭生产的颠覆性力量。从食物的加工、准备到孩子的养育,妇女在私人领域的生产和情感活动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难怪有学者将“五化”称作“一项了不起的解放妇女的试验”。遗憾的是,“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而关于失败的回忆往往是苦涩的,在曾经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从家务劳动中抽身出来的妇女们的记忆里,除了“可怜”的描述鲜有其他,虽然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盘桓在那个宏大的解放目标前面的同样巨大的困难:物资的奇缺,管理经验的不足,专业人员的缺乏。
重访社会主义
贺萧在书里努力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足够好”的故事,它超越了以往大多数关于集体化妇女研究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展示了妇女的生命轨迹与农村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包括讲述故事的历史节点。正如同在讨论“美德”的问题时,作者疑惑“如果访谈是在1955年(或1975年、1930年)”,妇女们回忆是否会有不同,什么时候谈论集体化对于妇女理解“集体化”、“社会主义”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贺萧对妇女们的访谈始于1996年,止于2006年,这时候的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呈现的是一派凋敝的景象:经济增长缓慢,农民负担严重,乡土道德文化沦丧,外出打工逐渐成为潮流。如此社会经济形态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妇女的记忆?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至少我们从书里看到,尽管妇女关于集体化时期的回忆大多是不满意的,她们的种种抱怨也并非总是针对集体制度本身。贺萧的研究没有或无法处理的是,如何辩证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集体化历史。比如,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能随着工分制的不断完善获得更好地落实。事实上,近年来的一些文献已经显示,到了1970年代,按件计工分在不少农村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少数坚持到今天的集体经济村庄则成功地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工分手册 来源:百度图片
《记忆的性别》是这个时代需要阅读的一本书籍。近些年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对“历史的终结”提出质疑,同时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整理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其内在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对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想象。重访社会主义不仅让我们明白历史如何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指引我们未来行进的方向。
参考资料: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全译)》,2018-03-08,作者:贺萧
原标题:这些奶奶们的悲欢记忆,为我们揭开不为人知的农村妇女解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