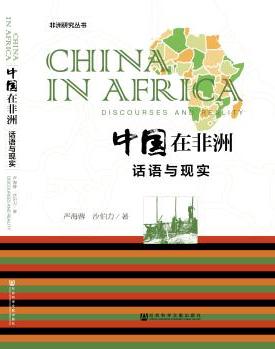从春晚小品想起,中国在非洲的前世今生
来源: 摘自《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 发布时间:2018-02-17 阅读:3810 次
导语:中国在非洲的形象经历过怎样的变迁?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曾与非洲人民同悲同喜同乐?请看今天我们推送的文章。
从“黄祸论”到“争取成为黑人”:华人移民的“色变”
中国人“走出去”、走进非洲有不同的前世今生。17世纪后半叶,荷兰人开始把印尼人、印度人、马达加斯加人当做奴隶运往非洲的开普敦,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把一些华人从印尼带去其在开普的殖民地,这些华人有些是犯人(往往因欠债入狱),有些是公司的奴隶。在荷兰人的开普殖民地( 1658-1795),这些华人与来自南亚、印尼的人们一起曾被视为“黑人。” 19世纪后半叶开始,约有两百万中国人陆续到达南非,其中一些是契约苦力,他们在新开发的金矿劳作。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和消亡,大量的中国人漂洋过海,去往东南亚的种植园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开发的金矿作苦力,或参与修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way),加拿大太平洋铁路(The Canadian Pacific),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
一战时期输出海外的华工(资料图)
1902年和1904年南非分别推出限制和禁止华人移民的法案。这也并非独特,而是顺应了当时欧洲关于东北亚的“黄祸”话语,跟随了当时新兴移民国家的排华潮流。十九世纪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明了“黄祸”一词,19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前期,不少西方的作家以黄祸入侵作为小说的题材。如1912年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创作了虚构的超级恶人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系列,他在1913年描绘了这位潜伏在大英帝国心脏伦敦、运行一个庞大的地下集团、时刻计划着颠覆大英帝国的清朝王族后裔形象: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它们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士的形象,他就是‘黄祸’的化身。
“黄祸”是西方的想象,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的话语建构。中国作家老舍在1920年代在伦敦居住了五年,这五年期间,他观察到了中国人被建构的过程: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黄祸论的建构事出有因。从1870年代到1960年代,西方出现了或在西方内部发生“种族”暴动、或有外部力量对西方进行“种族”入侵的文学政治主题。“黄祸”论即属于这类话语的一部分。这类主题的小说、电影描绘了黑人和亚裔或从内部攻陷或从外部占领“白人文明”的主要国家。很多这类主题的故事采取了一种回顾往事的形式,故事由未来21世纪或22世纪的某个人回忆19世纪或者20世纪的失败。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全球既有的种族等级遭到“他者”的颠覆。所以,“黄祸”论是西方的故事,在欧洲表达的是欧洲列强的统治精英对殖民体制及伴随殖民体制的种族等级制可能被颠覆的恐惧。
“黄祸论”是起源于19世纪主要针对亚洲黄种人的一种理论。资料图
在当时新兴的移民国家,“黄祸”作为话语手段功能有些不同,主要用来在多族群移民的过程中维护白人优越的地位。以南非为例,二十世纪初,南非白人商铺业主为了维护他们的垄断,压制华人商铺的竞争,向政府控诉华人,说华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严重的威胁”,代表了一种“恶在发展壮大。” 当时,南非印度人办的报纸发表了一个评论,嘲讽这一控诉,“如果允许华人商铺向华人出售日常必需品,这对欧裔的商人来说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是高度的不公正。这也等于欧裔的商人们承认他们完全无法跟华人竞争。”据猜测,这篇评论可能就是甘地本人写的。新兴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则一方面需要中国劳工,另一方面则先后出台了排华法案:美国的排华法案开始于1882年,加拿大的排华法案开始于1943年,澳大利亚的“白色澳大利亚政策”开始于1901年(针对华人和其他人群)。
1907年南非的殖民政府要求“亚洲人”用指纹印和其他个人信息进行特别登记,并要求他们携带通行证,为了抵制这一对“亚洲人”的歧视政策,不少中国人和印度人冒着被逮捕、监禁和遣返的危险,参与了消极抵抗运动 (passive resistance)。领导这场运动的有后来闻名于世的甘地,也有华人领袖Leung Quinn,这是甘地后来著名的消极抵抗运动的起源。南非殖民政府对包括华人在内的非白人进行了种种苛刻的歧视和限制,包括限制华人经商、禁止华人开矿。到了五十年代,在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华人和其它亚裔作为“有色人种”也遭到隔离。然而,为了引进日本投资,种族隔离政府把日本人视为“荣誉白人”,享有白人的特权。自80年代起,同样的“荣誉”被给予来自台湾的投资者。有些当地华人为了逃避种族隔离对他们无时无刻的限制,有时候也冒充台湾人,以图获得某些片刻的便利。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垮台,南非进入了民主时期、却同时也是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政权上的“民主化”和黑人的投票权并没有打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经济上两极分化的阶级隔离更加严重。在新世纪里,南非政府推出了安抚种族隔离受害群体的“黑人经济赋权法案”。不过,作为种族隔离受害群体之一的华人社群却不在法案覆盖的范围内。如果说在种族隔离时期,华人被排除在“白人”之外,现在华人发现他们又被排除在“黑人”之外。经过多次内部的讨论、辩论,华人社群终于在2007年起诉政府,为他们的再一次被歧视鸣不平。2008年高等法院终于裁决1994年已经定居南非的华人属于法案规定的“黑人”类别,享有“黑人经济赋权法案”的覆盖。
华人在南非的“色变”让人唏嘘,从早期被打入另册为“黑人”、到“有色人”兼偶尔冒充“荣誉白人”,到新世纪里争取成为“黑人”,所变的当然不是肤色,而是粘贴在肤色这个道具上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其意义,即种族化的内涵。南非华人的“色变”既见证了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的某种进步,又同时说明“种族”绝不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而是近代走向全球化的欧洲资本所主导的政治经济权力发明的一个范畴。随着资本在世界体系里积累的条件和方式发生转变以及国家权力的更迭,这一范畴发生着流变,但并未消失,更没有被否定。下面我们要说到,本世纪西方主流话语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也建构了一个“种族化”的框架,这一种族化的框架延伸和翻用了十九世纪的黄祸论。
西方媒体的“中国在非洲”话语建构:19世纪“黄祸论”的复归
2004年我们开始踏足南非,把南非当做我们认识华人进入非洲的近代起点。此后我们多多少少在十来个非洲国家进行过调研,从2007年开始,赞比亚成为我们的主要调研点。选择赞比亚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赞比亚的渊源: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援建了坦赞铁路。赞比亚于1964年独立,到六十年代末,国家开始把英美公司掌控的当地铜矿收归国有。在七十年代,卡翁达领导的赞比亚一边倡导社会主义,一边支持周边地区反白人殖民政权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为流亡人士提供避难所,因此也面临了当时周边南罗德尼西亚(今天津巴布韦)和南非白人政权的敌意。这条铁路的建设使得位于内陆的赞比亚能够突破当时南非和南罗德尼西亚的封锁,让她盛产的铜矿从新独立的、也在推动社会主义的坦桑尼亚出海。因此,这一铁路的修建支持了赞比亚的独立自主,也是第三世界团结和泛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见证,被称为“自由铁路”(Great Uhuru Railway,在斯瓦西里语里uhuru意思是自由)。
中、坦、赞三国工人一起修建坦赞铁路。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起步较早,始于九十年代,因此赞比亚是最早受到中国资本“走出去”影响的国家之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赞比亚成为西方报道“中国在非洲”的典型。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赞比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把国有的铜矿私有化,肢解成七大块分别招商引资,几家外资公司——来自加拿大、南非、印度/英国、瑞士、中国——因此成为赞比亚铜矿界的业主,这就是世界银行给赞比亚所谓“结构调整”的关键内容。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此时购买了赞比亚当时废弃多年的一个铜矿。结构调整对赞比亚最大的产业工人矿工的就业条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工人们失去了原来国有时代的铁饭碗,社会弥漫着不安全感和不满。在2006年大选前10个月,当时的反对党“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领袖迈克·萨塔开始对印度、黎巴嫩及中国籍商人发出警告——如果他当权,则会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稍后,萨塔在竞选策略上开始集中打“中国牌”,把人们的不满引向在赞比亚的中国人。
尽管来赞比亚的中国人在逐渐增多——在反对党竞选动员的高峰期2011年,赞比亚大约有1-2万中国人,但是中国人的人数和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被反对党信口开河地渲染夸大。这样的政治动员曾经引发过针对华人的小规模骚乱。通过电台、报纸和街头活动,反对党的这一话语营造和政治动员有六年之久,直至爱国阵线于2012年上台执政。在2006年至2012年间,赞比亚的反对党和西方媒体彼此呼应,把赞比亚变成了“中国在非洲”的典型。2012年后,虽然执政的爱国阵线领导人放弃了反华宣传,但是爱国阵线的一些官员仍然时不时地弹唱种族化的曲调。种族化的话语经过政治动员渗透到社会是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如果没有新的政治来促进社会利益和社会结构的进步,种族化的话语在现有的政治空气下仍然处于可发酵的状态。
在赞比亚,不少经历过卡翁达时代(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任期1964-1991)的人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有感情和记忆。他们当中一位早年在英国留学的、老练的政治家跟我们说,我们对欧美的制度很熟悉,很清楚,但我们跟中国打交道好像有云里雾里的感觉(cloud effect), 中国今天是什么呢?最近不幸因车祸去世的津巴布韦经济学家、非洲农业研究院(AIAS)创始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前主席山姆·莫约也曾尖锐地发问:今天所谓的新兴市场,本质上是顺从帝国主义的区域稳定力量(subservient regional stabilizer),还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这个问题因为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大量报道而变得越发不明朗。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和高层官员出席了这次峰会。西方主流媒体——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惊诧之后,显著地增加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报道,西方的精英也开始不断地评论“中国在非洲”,其中有大量并非无辜的误解。
在非洲的中国公司有各种形态和规模,在非洲中国的公司、小商贩、工人各有自身的利益和追求。举例来说,在赞比亚的中资企业就是 “由私有、半私有以及公有企业组成的混合体,其中涵盖了不同的企业规模和贸易领域。”在非洲的“中国商贸公司、个体企业家以及工人往往有自己私人规划,其盘算可能与(中国)国家和地区利益不同…。”但是西方主流话语建构的“中国在非洲”往往把中国政府、中国投资者、中国工人、中国商贩等等视为属于一个经过某种统筹的、有整体性的、由国家意旨主导的“中国(集团)”(China Inc.)。这种铁板一块的想象无视中国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同时共存、无视中国资本间的竞争、无视投资者和工人之间的差异、无视普通海外中国公民与国家(大使馆)的疏离。
在西方主流建构的这个话语世界里,“中国”是一个异类,碰到这个黑洞般异类,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和逻辑仿佛不能正常发挥,都失去了解释的功能。以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常常提及的一个话题为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访问非洲时重复了这个说法,就是中国建筑企业在非洲不雇佣当地劳工,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而喜欢大量雇佣中国人。实际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中国企业当然也追求利润,中国雇员的海外就业成本高于本地雇员,因此中国建筑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当然会雇佣当地员工。至于中国公司使用多少比例的中国员工,中国员工的数量和比例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变化,这是调研需要探究和解释的问题,也是本书的部分工作。结合当地社会的脉络,其实中国公司海外雇工的状况符合主流的市场经济逻辑和目的论,并不神秘。但是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笼罩下,中国公司不用当地劳工的说法一遍遍地被西方主流精英们臆想和重复。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权力生产了知识。此处我们可以加一句,权力也生产了臆想。
当一般的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关闭了解释功能,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解释“中国”的时候依靠的是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而在想象的意识流里,十九世纪的黄祸论沉渣泛起。剑桥大学学者艾玛·莫斯利对英国六家主要报纸2000-2007年期间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报道进行了文本收集和研究,发现媒体话语系统性地建构三种形象:非洲的羸弱、中国人的无情残忍、以及西方的托管人责任感。实际上,这三者的形象建构不限于英国媒体,而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共识。我们认为这样种族化的建构绝非偶然,也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消极残留,而是在新世纪的战略竞争中,西方主流精英对十九世纪“黄祸论”话语的调动和翻用。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在非洲”的话语里,傅满洲的鬼影又出现了。
西方主流或明或暗地把中国定性为“非洲的新殖民者”。这就是说,一向看好资本“全球化”的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这时却不承认中国资本和中国人员走出去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他们把“中国在非洲”排除在“全球化”之外,打入另册,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对其进行隔离处理。对于西方主流中的自由派来说,即便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者,它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破坏规范的异类,给西方在非洲的努力带来的障碍和麻烦。在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的话语里,全球化没有被问题化,资本没有被问题化,被问题化的是“中国在非洲”。我们认为,营造一个特殊的、吸引人眼球的“中国在非洲”问题是一个话语手段,由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问题被种族化为中国问题或中国人的问题,从而转移了批判的方向,遮蔽和保护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体系。
回到前面山姆·莫约的发问:今天所谓的新兴市场,本质上是顺从帝国主义的区域稳定力量,还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在我们看来,中国在非洲既是顺从的区域稳定力量,也对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中国的工业化既包括了毛时代的自主工业化(今天这部分主要体现为国有资本),也包括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依附性工业化,即通过引进外资形成的融入全球垄断资本产业链的加工工业。今天被西方看成威胁的是前者。中国资本“走出去”是八十年代 “请进来”在逻辑上的衍生。“请进来”引进大量外资,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使经济外向化。在改革开放20年之际,中国已经资本过剩、产能过剩,资本积累遭遇瓶颈,中国资本便开始“走出去” 寻求海外原料和市场。而中国资本走出去在时间点上也正是“华盛顿共识”集团利用非洲国家的债务,胁迫非洲国家进行结构调整,开放投资和贸易、变卖国有资产的时候。所以,西方没有料到的是,“华盛顿共识”也为中国资本进入非洲开了大门,中国资本也成为“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获益者,尽管西方资本获益更大。因此,中国资本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是既得利益者。
文章来源:摘自严海蓉、沙伯力著作《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小标题是澎湃新闻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