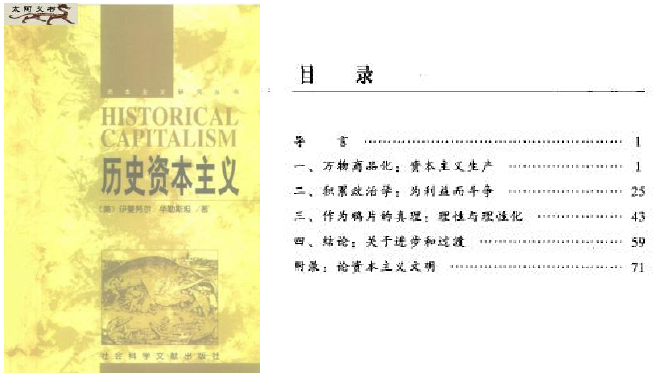活在利润至上的世界里,太累、太难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8-08-04 阅读:3508 次
导语:成功的少数,永远是由不成功的多数来陪衬的。利润为本超越了以人为本,全面掌控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活不好的人口数字大大攀升了。
《我不是药神》的主角程勇,长期挣扎在利润逻辑的重压之下,在接触白血病人的过程中间,为此去开辟仿制药进口渠道,并因此偶然地变成了成功人士,与病人的密切互动也激活了他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最后实现了人的觉醒——明白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东西。此后,程勇就不自觉地与利润唯一正确的经济和政治法律逻辑杠上了,最终受到法律制裁蹲了三年班房。
在这个故事中间,“利润很正确”与“活着太沉重”的对照,十分发人深省。这这样的社会中间,一个人想要活得好,就需要在“利润攫取”的道路上多走一段路才行,但是“利润攫取”越是成功,作为利润攫取对象的消费者就活不好了。
一、资本社会里人的异化:生产者利益反对消费者利益
利润越是正确,对生活成本的掌控越是全面,活不好的人口数字就会大大攀升,这其实就是中国四十多年来新构建出来的一般人的生存境况。在这社会里,成功的少数,永远是由不成功的多数来陪衬的。
程勇最初作为一个不成功的商贩,因为在生产者角色地位上的不成功,未能攫取足够的金钱,结果,不仅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家庭还有老婆,最后也没有留住自己挚爱的儿子。看起来,程勇作为不成功的生产者,未能对“利润攫取过程”做出足够的贡献,这不仅使得他难于成为合格的消费者,甚至还难于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在资本社会的利润逻辑之下,一个人的合格性主要是与利润实现能力和分红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达不到配做人的条件。
每个人的生存,同时还必须是消费者,在这里每一个消费者,都受到攫取尽可能多利润的生产者的抑制。靠吃药续命的白血病人群体,看起来像是纯粹的消费者群体,而购买力不达标、不合格的消费者就不配享有生存机会,这通过故事设计格外清晰地被呈现出来了。
在资本全面掌控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成功还是不成功,主要是与他对利润做出的贡献和获得相应分红的状况来决定的。由此,也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有足够购买力的、合格的消费者;甚至于作为人的社会角色的合格性,都要由他的利润贡献度和分化状况来检验:正因为如此,资本社会中间,对人的异化改造,首先在于生产角色(要参与到利润榨取过程中去还需要就此获得成功)与消费角色的分离。而一个人作为生产角色的行为选择,需要承接消费角色地位上的压力传递——需要卖力地去争取成为一个成功的生产者,否则就成不了合格的消费者。如同主角程勇那样,因为卖印度神油的不成功,结果连店面房租都交不起,家庭也保不住。正因为如此,人作为生产者首先要承接“追求成为合格消费者”的压力,去积极主动地服务于追逐利润的生产者逻辑,就这样,资本和利润逻辑就被个体潜在地正当化和内在化了,主动选择成为利润生产和实现链条上的一个“合格螺丝钉”。
生产者的利益诉求与消费者利益诉求不兼容,这是资本社会人性普遍异化的起点和最牢固基础,由此,不成功的生产者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生产者利益诉求中间,合法的利润实现具有最高正确性,这是资本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逻辑,由合格消费者要求去先在地界定生产者的追求和方向,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最主要动机。同时,资本追求的利润逻辑渗透到政治和法律秩序内部,也成为唯一具有正确性的司法逻辑:谁不尊重利润实现的逻辑就要受到司法制裁。
在这里,一个成功的生产者总是联系着多数失败的消费者,利润攫取机会的稀缺性,决定了生产者角色与消费者角色的冲突程度。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成功机会,那当然就皆大欢喜了。但是,成功机会从未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成功机会越是稀缺,成功的生产者对于消费者的压榨力度就越是难于容忍,少数人妨碍多数人的状况就越是明显。在资本社会里,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分化和对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肯定会被彻底消解,这种服务精神即便偶然被激活,看起来也无济于事,正如张常林教育程勇所嘲讽的“你还真的治得了穷病”。
在资本社会中间,生产者角色反对消费者的基本利益的状况,个人作为生产者要服务于利润创造并由此获得分红机会,这不仅造成异化,还显著地压制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为利润而生产的逻辑,替代和压制了“为人民服务”的逻辑,越是人均资源不足,就越是显著地抑制了生产扩张的潜力,更高地造成了异化。
二、在利润很正确的资本社会里当一个病人
在中特资本社会中间,一切服务和产品的生产都围绕着利润目标而进行着,这个近四十年来构建的新状况,已经是一切人工作和生活的主要背景了。除了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偶尔挣脱之外,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得服从利润的逻辑,而且,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业已按照利润逻辑进行了重新打造,连我们的头脑也被较为彻底地规训为信仰利润才具有唯一正确性了。
资本统治社会的深化,根本上完成了对人们生存成本的重组,格式化了我们的头脑,用利润攫取逻辑去改造一切生产过程,结果是清楚的,这固然塑造了一些成功者,但更多被塑造出来的是失败者。在今日中国,除非特别有权或者特别有钱,活着都已经不那么轻快了。
程勇作为失败的生产者,与白血病人这个纯粹消费者群体困境相遇之后,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就展开了。程勇开辟了从印度走私仿制救命药的地下通道,获得了仿制药的中国代理权和定价权。由此,改变了从前那种失败生产者的地位,走上了发财致富的道路,这是故事的上升波。
按照海外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逻辑是攫取各种“经济租”或者“垄断租”。如果从过去四十年来我国资本的构建经验看,利用各色垄断条件去扩大租金数额,是最主要的努力方向。能否开辟攫取“经济租”的机会,对于一个成功的生产者而言至关重要。程勇亲赴印度寻找货源,开辟走私通道,打造地下分销网络,然后,通过这样的“走私渠道垄断”,找到了一个攫取经济租的机会,然后就改变自己的不成功生产者地位。
程勇的成功是偶然的例外,主流医疗事业是最典型的买卖方信息不对称市场,卖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尽可能榨取买方的剩余价值,并提高经济租租额,如果再叠加了各种行政管制的加成,就更有利于在普遍的经济租租额基础上,方便地加上垄断租额了。在今日中国的医疗市场上,优质医疗资源(各地各种名牌大医院)具有较为显著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实际上的卖方市场地位,因而也就拥有实际上的单方定价权。这些大医院在医疗市场上起到一种价格领袖的作用,透过拉高定价的方式,落实信息不对称所隐含的榨取消费者剩余价值的潜力。这是与程勇相对照的主流医疗事业攫取“经济租”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行政管制机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站在消费者一边,管制各种榨取消费者剩余价值的定价方式,遏止经济租的扩大;二是反过来参与进去,帮助促进医疗卖方实现更快速更大规模的榨取。就目前来看,后一种是主要的和长期的努力方向,前一种努力方向主要停留在口头上。撇开圈钱勾结的小圈子套路不论,其实还可以务实地追问一下:在利润很正确的舆论氛围中间,行政管制拒绝与利润合谋的可能性有多少?换言之,在医院基于信息不对称营造的攫取“经济租”链条中间,行政管制机构的选择,更多的是去创造“经济租”加成条件,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如此,才在医疗行业中间实现了惊人的GDP数字大跃进。1978年中国用110亿元的卫生事业费,有效地覆盖了90%以上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到了2017年同一个费用数字膨胀了470倍之后,80%以上人口失去了曾经很有效的低成本低水平保障网络,“看病难吃药贵”成为大多数人口的一个沉重负担。
中国“新三座大山”的重新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租和垄断租不断提高的过程,民众生存成本被日益拉高,大多数人挣不够体面生活的收入。其中,住房是土地区位的自然垄断叠加了行政垄断,还得到金融资本的鼎力扶持之后,很短时间内就拉升到绝大多数人不敢仰望的高度上。今日中国教育的易得性增加,但对于个体和家庭有意义的优质教育资源——有助于个人向上流动的高升学率名校教育,却是稀缺资源,其购买价格也一样是处在绝大多数人口无法企及的高度上。各种“大山”作为经济租的榨取路径,多体现出行政管制加成市场垄断地位,帮助实现经济租的最大化榨取,结果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经济租攫取力度,超过大多数人口最高负担能力的状况。
《我不是药神》通过对主角程勇的故事展开,真实而具体地揭示了在当前社会里,利润很正确,经济租攫取很顺利,但个体的生存却十分不易,活着太沉重了。电影的故事相对丰满,能够成功地激活观众自身的工作和生存体验,在情节展开中间,让观众深切体会到“利润很正确”VS“活着太沉重”的严苛对照。而利润的正确性,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掌控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存成本,还成为政治和司法的唯一正确标准,甚至还是我们头脑思考社会状况的唯一标准,正是因为利润唯一正确这个隐含的政治法律逻辑,使得程勇不得不被抓、被判,在得到宽大之后还蹲了三年大牢。
三、被规训的头脑: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
沃勒斯坦在《历史资本主义》一书中间,用了这样一些鲜明的标题来讲述资本主义的特点:万物商品化、积累政治学、作为鸦片的真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间,一切都商品化了,事关人生存机会的医疗和药品也是如此。同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作,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需要被改造为保护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同时出于降低司法和制度维护成本的需要,迫切需要民众的认同,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普通民众也认定除此之外别无正确路径,让全民都坚定地将此奉为真理,就像全民都上了鸦片的瘾一样,这就是主流经济学这些年来着力经营的“全民鸦片瘾”——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方式不仅能够促进GDP数字高涨,还将有助于一切人的福利改进;而保护私有产权和专利,是保证技术创新有序进行的关键。一句话,没有对于资本家和利润实现的可靠保护,就没有技术进步和GDP高涨和全民福利改进。这样的鸦片真理推销过程,肯定会把个体作为利润生产链条上“合格螺丝钉”的角色体验,结合进去并产生说服效果。
鸦片真理的推销事业成就,也体现在《我不是药神》的观后感中间,一些人之所以表现出极端信奉“鸦片真理”的状况,认为如果没有对专利和垄断价格的保护,药厂就不会愿意研发新药,“格列宁”就不会产生了。作为鸦片的真理中间,最受到信奉的逻辑,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生产中间投入最大宣传成本的逻辑,这些意识形态认为各种经济租的存在,是为了让企业投入产出能够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没有了利润企业就不会生产和研发,人类就要完蛋了。应该说,基于技术发明创造的技术垄断地位所支撑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由此获得的定价权和技术租,算是最符合资本社会意识形态生产逻辑的最后一根稻草。换句话说,在攫取经济租的利润逻辑中间,开发新技术和由此形成垄断地位及其租金攫取,是仅有的一种“外部性为正”的状况。
即便如此,真实的技术发明过程,新产品技术的成熟,都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的投入与开发过程能够涵盖的了,不是一个孤立的追求利润单位所能够“内部化”的了。就拿治疗白血病的神药格列卫来说,在理论方面就沉积了前人130多年的认识进步过程,而在新药开发二十多年的历程中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先期投入,相当大一部分成本是在企业外部的政府投入过程中间完成的。这个状况,恰好说明私有企业或者各类以利润追求为最高目标的生产方式,都不再是支撑技术进步和人类福祉提升的合理制度了。
这一点尤为明显:不仅仅生产及其产品后果是高度社会化的,而且真正的技术进步过程其实也早就高度社会化了,用私人化的利润目标去统合技术开发和生产过程,其局限性被日益放大了,很难“内部化”新技术开发所需的理论认识进步和技术开发不确定性。在这里,最符合意识形态对技术租的正当化辩护的技术垄断租金方面,也明显呈现出说服力的严重不足,相反,现在应该务实地反过来看问题。
更何况,信息网络和大数据的兴起,恰好可以在另一面支持集合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合作过程,有利于生产者在患者和医疗机构积累的大数据信息基础上,选择更合理的技术路线,窄化技术开发选项,缩短开发进程并降低失败风险,一句话,有助于低成本实现新技术的突破。但是,只要是资本社会的生产方式中间,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利益分离的藩篱打不破,高度合作的技术路线在现实中间就无法成立,甚至此种新的技术开发路径——大量应用病患信息去支持新药技术开发——在伦理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技术开发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实际上是过时的生产方式中间在起阻碍作用,放大了成本和风险,同时还降低了新技术的成功率,这显著不利于合作水平提升和新技术开发成本的下降。
古巴抗癌药品的成功开发路径,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其实,古巴仅仅由于能够实现新药开发与病患需要的紧密结合,排除了利润逻辑,就取得了较大成绩。实际上,由于古巴人口基数较小,其新药开发能够得到病患信息数据还很有限,如非如此,还能够更显著地提高新技术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四、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内容:破碎且不连续
对于人自身而言,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穷病”普遍化了,更为严重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内容,都慢慢地成了稀缺品。甚至,亲情也日渐稀薄且难以维持了,做人的基本尊严也成了稀缺品。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穷人,在人生意义或者价值生产领域也变得日益穷困了,有时候甚至是不得不自己出手,主动割断亲情以免自己成为家人的拖累。
意义生产的穷困,不仅表现为稀少和难以得到,还表现为欠缺合理的表达方式。在电影中间,亲情、血脉传递、人的尊严等等,看起来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需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的表达,缺乏像利润生产那种明晰连贯的表达方式。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容,相对于利润生产的逻辑,不仅在现实社会中间被边缘化,连通过故事去想象和表达出来,都显得破碎和不连续了。
在电影中间,一个白血病人黄毛,为避免成为家人的负担,不得不离家出走并且决绝地断开与亲人的联系,这种选择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很难进行评判。等到他有了希望之后,并受到程勇的劝说,才打算回家见见父母亲人,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回家去,在他的遗物中间留下一张买好的回家火车票。
白血病人吕受益原本打算自杀,避免拖累家人,因为看到儿子降生,由此激发了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曾经奢望过“说不定可以看到小家伙结婚”。为此,他去动员卖印度神油的程勇,开辟印度仿制药的走私通道,等到走私廉价药渠道被截断之后,生存的希望断绝,他为避免进一步拖累家人,带着对妻儿的无限眷恋跳楼自杀了。
有一次程勇喝高了之后,坚决要求送思慧回家,不对称的地位落差,使得思慧难于拒绝,在最后阶段,程勇放弃了。这个情节,似乎隐晦地写出,人的尊严是何等稀缺,尤其是存在着“有求于人”条件下,人的尊严是很难维护的。似乎仅仅因为程勇的良心发现,才自上而下地给出了对思慧的尊重,这个令人心酸的情节,其实反映出资本社会中间,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下层人士的尊严往往操在上层人士手上,是否能够得到起码的尊重,要视上层人士的选择。
程勇在参加了吕受益的葬礼之后,走过白血病人排成的队列,被对生命的敬畏这种非主流情感强烈刺激,还因此激活了对生命的敬畏,重新捡回走私廉价仿制药的路子,再服务于白血病人的生存希望,由此,埋下了被法律制裁的隐患。在去监狱的警察上,程勇看到了很多前来送行的病人,他似乎由此收回了“心理报酬”并收到了源自人生意义网络的显著激励,甚至他还看到了死去的黄毛和吕受益,都站在送行人群里跟他对眼神,看起来,一个人对生命的敬畏和由此付出的服务,所能够得到的心理报酬,可以跨越“阴阳两隔”的那种距离。
人生意义网络的编织和对心理报酬的意外体验,相对于真实社会中间利润逻辑的强大和唯一正确性的压制,通常是很难有机会编织和营造出来的。程勇参与这个人生意义编织过程,先是出于一个不自觉的选择(希望借此挣钱发财),然后走向了自觉(贴钱做走私),最终倒了大霉,说明现实社会中间超出利润逻辑去关注人的需要和人生意义网络,只能够是极其偶然的意外状况。
在电影情节中间,白血病人整日“计钱续命”——哪一天没有钱,那一天就很快没命,廉价走私药“格列宁”的到来,才延长了病人活下去的希望。正是因为人的生存境况如此严酷,就不得不高度质疑到利润的唯一正确性逻辑,各色人等也都不得不对生命和生存机会表现出起码的敬意。主角程勇如此,曹警官如此,乃至于法院量刑也需要给予从轻或者减轻考虑,这样的情节安排,故事编导也许原本是希望由此顺利过审,但是,却较为含蓄地凸显出各色人等“对生命本应该有的敬畏之情”,并由此对照出利润逻辑的强大性。有人指出,此种处理方式是对“大圆满结局”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妥协,但由于此种客观对照的存在,就有了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感,此种淡化和妥协安排不仅没有损坏主题,反而深化了主题。
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原本应该是人类各种制度的唯一旨归,但由于受到强大的利润逻辑正确性的压制,对于生命的敬畏变成了偷偷摸摸的行为,变成了那种不绝如缕的清风,去悄悄地滋润人们日渐枯竭的心田。这个故事中间近乎没有坏人,包括警察也偷偷表现出尊重生命需要,但是,正因为如此,恰好在反面凸显出利润唯一正确的逻辑之强大。
看起来,要戒掉沉迷于“鸦片真理”的“烟瘾”,让思想冲破牢笼,现在有了空前的重要性。追问和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需要,追问这些需要有没有更好的路径,认真思考有没有利润逻辑主导下的其他路径,这看起来日益重要。或许,这样来思考的人多了,程勇“做好事进监狱”的悲剧,才会被终结,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需要,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尊重和满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