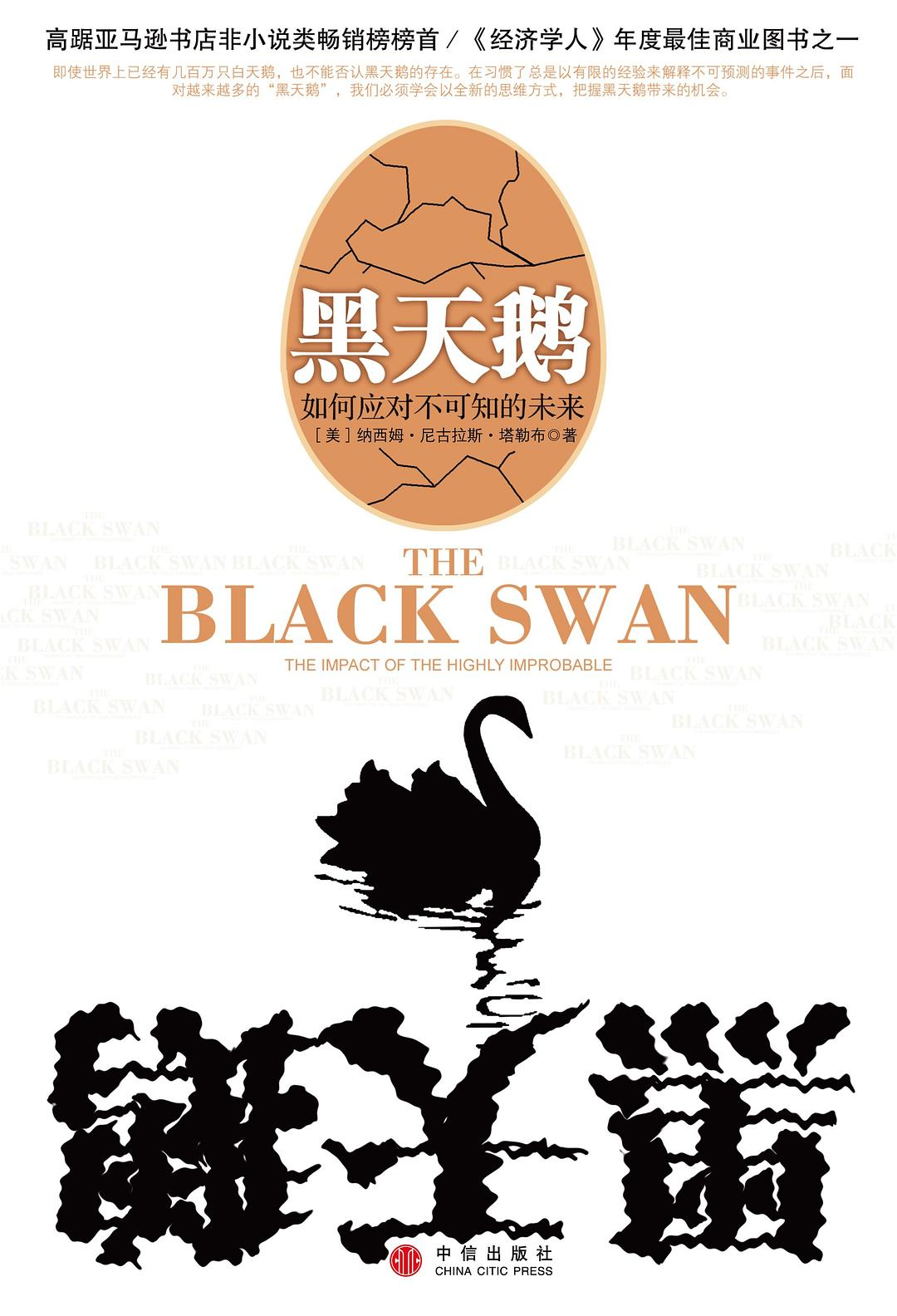2020疫情系列|新冠病毒与资本循环
来源: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发布时间:2020-04-12 阅读:4743 次
食物主权按:
疫情引发的危机之后,不同的分析模型都试图预测疫情的走向,指导对疫情的控制。然而,Rob Wallace等强调,更重要的是在改变导致疫情爆发的深层结构性因素:资本化、工业化的农业既深刻地改变了生态系统,释放出病毒,也制造出加速病毒演化的条件。譬如,他们指出,单一种植、单一养殖在减少多样性的同时也消除了病毒传播的屏障。工业化农业改变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布局,让病毒更容易在全球化的流动链条中扩散。简而言之,资本化的农业和公共卫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作者们提出,只有去除资本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压迫和异化,才是对抗病毒的最根本的措施。
本文中,作者们接受了新冠病毒是通过食物供应链传播到人类这一说法。目前这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有研究者已经提出质疑[1]。然而,不论具体的传播路径如何,本文作者们对资本化农业与生态关系的分析,深刻入理,意义宏远。
感谢Wallace博士授权食物主权翻译此文。原英文链接见文末。
作者|Rob Wallace, Alex Liebman, Luis Fernando Chaves, Rodrick Wallace
翻译|佳惠、坚如、羽婷、好运
校对 | 侯牛、侯怡
排版|童话
作者简介:
Rob Wallace是一位进化流行病学家,他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均担任过咨询顾问。
Alex Liebman是罗格斯大学人文地理学的博士生,拥有明尼苏达大学农学硕士学位。
Luis Fernando Chaves是一名疾病生态学家,也是哥斯达黎加营养健康研究与教育中心的高等研究员。
Rodrick Wallace是纽约州精神病研究机构传染病部门的科学家,该机构位于哥伦比亚大学。
以上几位科学专业人士都非常赞赏Kenichi Okamoto的充满洞察力的评论。
1、关注统计模型vs.关注疫情的结构性成因
COVID-19是由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疾病,同时也是自2002年以来第二严重的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如今已肆虐于全世界。截至3月下旬,一个又一个医院在病人激增中陷入医疗堵塞,无数个喧嚣城市中,人们在家中避难。
最初的爆发地中国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韩国和新加坡也是如此。但是在欧洲,尤其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就已经快要被死亡的重担压垮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病例刚刚开始累积,有些国家准备得比其他国家更充分。而美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近期的境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疾病在美国国内要到5月份才会达到高峰,医疗保健工作者和病人们已经开始争夺越来越少的个人防护设备。令人震惊的是,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建议护士们使用头巾和围巾作为口罩,护士们宣称“这个(医疗)系统要完蛋了。”
与此同时,美联邦政府以比各州更高的价格来购入基本医疗设备(最开始联邦政府还拒绝为各州购买这些设备)。在病毒因政策不当已经在国内肆虐之时,美联邦居然宣布,可以将边境封锁用作公共卫生领域的干预措施。
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个流行病学小组预测,目前缓解疫情的最佳方案,即通过隔离已发现的病例和老年人来减少病例增加,即使在美国成功实现,美国也仍将面临110万人的死亡,而且最终的病例负担是美国重症监护病床总数的8倍。只有把美国疾病防控变为中国式的检疫和社区隔离,包括关闭各类机构,才能将死亡人数降低到20万左右。
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学小组估计,防控要成功,至少要持续18个月。这将导致经济萎缩和社区服务衰退。由于大量的紧急护理床位已经满员,该小组提议通过在开启和暂停社区隔离模式中来回切换,来平衡疾病防控和经济的需求。
但其他流行病模型的推崇者并不赞同上述看法。以《黑天鹅》这本书闻名的Nassim Taleb为首的一个团体宣称,帝国理工学院小组的模型未能囊括接触追踪和挨家挨户的监控。但是,Taleb团队其实并没有考虑到,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范围,早已越过了许多政府能防守的警戒线。只有在疫情开始缓和,而且测试的准确性很高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才会采取Taleb团队建议的措施。正如有些人开玩笑说道:“冠状病毒太激进了。美国需要一种更温和的病毒,这样我们可以逐步应对。”
Taleb团队注意到帝国学院小组并没有研究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消灭病毒。所谓消灭病毒,并不意味着零病例,而是通过足够的隔离措施,使单个病例不能产生新的感染链。在中国,与病例密切接触的易感人群中,只有5%的人随后被感染。Taleb团队非常支持中国的防控计划——全力以赴,以足够快的速度将疫情消灭,而不是陷入在疾病防控和确保经济不因劳动力短缺而衰退之间摇摆,将抗疫变成马拉松长跑。换句话说,中国严格的(和资源密集型的)防控方法把她的人民从帝国理工学院小组推荐的(也是目前其他国家进行的)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隔离中解放出来。
流行病学家Rodrick Wallace(我们中的一员)完全颠覆了既有的模型。上述的两种模型都是用来应对紧急危机的。无论它们多么有必要,都忽视了危机从何时何地开始的问题。事实上,结构性因素也是危机的组成部分。考虑这些结构性原因,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最好地应对危险,而不仅仅是重启本就造成目前困境的经济。Wallace写道:
如果给防火员足够多的资源,在正常情况下,常见的大多数火灾,都可以被控制,伤亡和财产损失也也可以降到最低。然而,这种标准严重依赖于一种不那么浪漫,但同样英勇的工作,那就是持续不断的监管努力,通过制定和执行规范来限制建筑危害,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消防、卫生和建筑保护资源.... 也就是说,大环境对大规模流行病的传播情况至关重要。
如果要在不久的将来避免真正的大规模致命性流行病,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允许跨国农业企业将利润私有化,同时却将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的政治结构。比如使其重新将这些成本内部化。
对疫情的疏于防备和反应失败并不仅仅始于去年12月,也并不始于武汉爆发疫情后其他国家仍然反应迟钝。在美国,失败并不始于特朗普解散流行病准备小组或让700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位空缺着。失败也不始于联邦政府未能对2017年流行病模拟结果采取行动,也不始于美国“在病毒爆发前几个月削减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国的专家职位”(尽管美国专家错过了在中国的早期直接调查,削弱了其应对能力)。失败也不始于拒绝使用WHO提供的检测试剂盒的错误决定。尽管早期信息的延迟和测试的彻底失败,无疑将导致许多人(可能是数千人)失去生命,但这些都不是失败的开始。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从那时起,政府就忽视公共卫生事业,任由公共卫生沦为盈利的工具。一个国家,被个人主义俘虏,即使在正常时期都没有足够的呼吸机和医院床位来服务病人,是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集中必要的资源来进行传染病控制的。
疾病生态学家Luis Fernando Chaves(这篇文章的另一位合著者)的态度更加明确。他以Taleb团队的观点为基础,并参照了生物学家Richard Levins和 Richard Lewontin的看法,认为“让数字说话”的模型遮蔽了很多预设。帝国理工小组的模型,将分析范围限制在狭义问题上。他们故意不去分析那些更为重要的、推动疫情爆发的市场规律和作为干预基础的政治决策。
不管是否故意,这些分析模型都把保障大家的健康排在第二位。如果一个国家在控制疾病,还是保障经济之间摇摆不定,成千上万最脆弱的人就会因此丧命。福柯关于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人口采取行动的观点,尽管更温和,但也只是更新了马尔萨斯学派坚持群体免疫的观点——英国保守党政府和现在的荷兰政府都提出了这个建议——让病毒在人口中不受阻碍地蔓延。除了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希望,几乎没有其他证据能保证群体免疫将保证阻止疫情爆发。事实上,病毒很可能会突破人群的免疫层。
2、从干预疫情到反思“野味”的商品化供销链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以正确的方式应对紧急情况,要求我们同时面对需求和风险。
我们需要将医院收归国有,就像西班牙在应对疫情时所做的那样。我们需要像塞内加尔那样进行快速的、大规模检测。我们需要将药品社会化,让大家用得起药。我们需要对医务人员实施最大限度的保护,避免他们被感染。我们必须把修理呼吸器和其他医疗机械的权力掌握在手里。我们需要开始大规模生产各种抗病毒药物,如remdesivir和抗疟的老药氯喹以及任何看起来有希望的其他药物,同时进行临床试验,测试它们在实验室之外是否有效。我们应实施有效的计划:(1)要求企业生产卫生保健人员所需的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设备;(2)优先把它们分配给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必须建立一批大规模的流行病防治队伍,提供从研究到护理的工作力量,以回应病毒(和任何其他病原体)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病例数量要能够和危重症床位、人员配备和必要的设备相匹配,这样就可缓解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假设暂时挺过病毒的攻击,然后就再去实施接触者追踪和病例隔离,从而将疫情控制在医疗系统承载能力极限以下。我们必须要立刻派出足够的人手,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地排查病例,并为工作人员配备所需的防护装备,比如充足的口罩。同时,我们要改变社会的组织形式,让人们在病毒消失之后,能够更好的生活。
然而,在这样的计划得以实施之前,大多数民众都几乎被抛弃了。除了继续向顽抗的政府施加压力,本着150年以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精神传统(尽管可能已经丧失殆尽),人们应尽量加入新兴的互助组织和街道组织。工会应该聘请专业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对这些团体进行培训,以使得那些组织提高对病毒的认识和警惕,防止病毒扩散。
我们坚持,应对危机的模型,需要考虑病毒的结构性起源的问题。这是能够逐步保护人民的关键,是实现人民优先于利润的关键。
很多人把疫情的出现归咎于出乎意料的疯狂行为(例如吃蝙蝠),这种说法如果被正常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一消息最初带给我们的惊愕,即一种SARS病毒离开了它的野生动物避难所,仅仅大约8个星期后便在人类之间传播。在地区传播路线末端,病毒出现在异域美食的供应链中,在中国武汉,它成功地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武汉这里,病毒不仅在本地扩散,而且通过飞机和火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交通网络结构中的扩散,以及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实现了在地理层次结构中的扩散。
很多人除了用典型的东方主义描述野生食品市场外,很少关注一个明显的问题:在武汉最大的市场里,野生动物这种奇异的食品行业如何在传统牲畜行业旁边进行销售的呢?这些动物并没有在卡车后面或小巷里被销售,销售者是有许可的。事实上,除了渔业之外,世界范围内的野生食品生产正日益正式化。而且,这个资本化的过程,都是由那些支持工业生产资源推动的。尽管在产出规模上与传统食品工业相差甚远,但这种区别现在也缩小了。
重叠的经济地理(小生产与资本化的生产相重叠)从武汉市场一直延伸到内陆地区,在那里,野味和土产品是在不断缩小的边缘中生产的。由于工业生产侵占了最后一片森林,野生食品企业必须进一步深入荒野,来增加供应和扩大销售。结果,最奇异的病原体,例如由蝙蝠携带的SARS-2,从食用动物和在照料它们的工人身上找到它们传播的路径。
3、资本为牟利破坏自然,为病毒渗透人类社会打开方便之门
病毒的渗透路径值得详细分析,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疫情期间制定计划,而且有助于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把自己推入这样一个困境的。
许多病原体来自于食物生产中心,例如属于食源性细菌的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但许多像COVID-19这样的病原体都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边缘。事实上,至少有60%的新型人类病原体是通过从野生动物传播到当地的人类社区而产生的。
一些环境科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有些由高露洁和强生公司(积极参与农业综合企业主导的森林砍伐的两家公司)资助,根据1940年以来的疾病爆发,绘制了全球地图,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判断,即新的病原体可能会定向发展。在绘制的地图上,颜色越温暖,就表示那里就越有可能出现新的病原体,因此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会成为红色热点。但除了这种“绝对性地理”导致的混淆以外,该团队还漏掉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关注疫区,却忽视了塑造流行病的全球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共同关系。在全球的欠发达地区,为了发展和生产,导致土地使用发生变化和疾病出现。人们很容易将疾病暴发的责任归咎于土著居民及其所谓的“肮脏”文化习俗。例如食用野味和土葬被认为是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两种做法。和那些科学家的判断相反,我们则通过建立“关联性地理”,发现全球资本的主要来源纽约、伦敦和香港将变成世界上三个最糟糕的热点地区。
与此同时,疫情爆发地区甚至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政治制度来组织抗疫。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将最严重的破坏从规模化农业转移到全球不发达地区——已经从由国家主导的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方式,变为跨越国企业和各种商品流通组成的新综合体。农业综合企业正在重新组织它们的剥削形式,使其成为横跨各国的不连续的网络。例如,现在有许多跨国的“大豆共和国”,分布在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公司改变了管理结构、资本化、分包、供应链替代、租赁、跨国土地集中以适应这种新的地理环境。在跨越国家边界的过程中,这些“商品国家”灵活地嵌入不同的生态和政治边界,新的流行病也由此产生。
例如,尽管从商品化的农村地区向城市贫民窟的人口流动到今天仍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但在城乡二元讨论中被忽视的是农村范围内的劳动以及变成“城中村”(periurban desakotas)或者“中间城市”(zwischenstadt)的农村城镇的迅速增长。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等人已经确定了这些新近的城市化的景观如何既充当了本地市场,又成为了全球农产品流通的区域枢纽。这样的地区中,一些甚至进入了“后农业时代”。这就导致了森林病害动态以及病原体的源头已不再局限于腹地。与它们相关的流行病学已经转变为关联性的,在时空上都是如此。一株SARS病毒可能会突然从蝙蝠洞穴中逃出来,并且迅速传染给居住在大城市的人类。
这些“野生的”病毒所在的生态系统曾经部分地受热带森林的复杂性所控制。现在,一方面是资本主导的森林砍伐,一方面是城镇化进程,以及公众健康和环境卫生的缺乏,这个生态系统正在急剧地缩减。在森林病原体与其寄主物种一起消亡的同时,曾经一度在森林中会迅速消亡的感染子集——除非以不合常规的速度遇到其典型寄主物种——如今正在易感人群中传播。在城市中,财政紧缩的政策和败坏的法规导致人们遭受感染的几率大大增加。即使有有效的疫苗,疾病的爆发也会有更大范围,更长的持续时间和更强劲的势头。曾经可能只是局部范围的“溢出事件”,现在则成为通过全球贸易和旅行网络而散播的传染病。
2019年9月30日,刚果(金)国家公园遭砍伐破坏
由于改变了环境背景——诸如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疟疾和黄热病之类等进化相对不多的老面孔,都已经急剧转变为区域性的威胁。病毒突然一次又一次地从偏远的村民群体溢出,逐渐在首都城市感染了成千上万人。在生态学的另一种方向上,甚至长期以来,充当疾病收储库的野生动物也正在遭受冲击。由于森林砍伐,原生新世界猴【编注:也叫新大陆猴,因在美洲新大陆被发现而得名,包含分布在中美洲、南美洲和墨西哥等热带地区的五个灵长类动物科的小目】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易受野生型黄热病侵袭,并且至少接触了这种病毒百年的它们,正在丧失他们的畜群免疫力,目前已有数十万死亡。
新世界猴受黄热病侵袭
4、生态体系被破坏后,人类免疫力的调整速度赶得上病毒寻求生路的速度吗?
从病毒的全球传播角度看,商品化农业既是传播的推动力,也是各类病原体从最偏远的收储库迁移到最国际化的人口中心的途径。新的病原体正是通过商品化的农业,沿途渗透进农业社区的门户。相关的供应链越长,周围的森林砍伐的程度越大,进入食物链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就会越发多样化(病原体本身也更加罕见)。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在最近出现或者卷土重来的、来自农村以及食源性的病原体就包括了猪瘟、弯曲杆菌、隐孢子虫、环孢菌、埃博拉雷斯顿、大肠杆菌O157:H7型、口蹄疫、戊型肝炎、李斯特菌、Nipah病毒、Q型流感、沙门氏菌、弧菌、耶尔森氏菌以及一系列新型变异流感,包括H1N1(2009),H1N2v,H3N2v,H5N1,H5N2,H5Nx,H6N1,H7N1,H7N3,H7N7,H7N9和H9N2。
尽管并非故意,但整个产业链的组织和活动都加速了病原体毒力的进化以及其随后传播。日益扩张的单一种植和养殖消减了免疫防火墙。这就让本可在多样的种群中减慢传播速度的病毒没有了屏障。于是,病原体可以针对常见宿主的免疫基因快速进化。同时,规模养殖下,拥挤的生存条件降低了免疫反应的发生概率。更大的养殖规模,更高的工业化农场的密度,导致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反复感染。工业化生产追求高产、大批量,因此给畜舍、农场、地区层面都不断重复产生易感的动物,这消除了病原体“致命性”进化的上限。密集养殖也会最大程度地“奖励”那些传播最高效的病毒株。将鸡的屠宰年龄降低到六周,很可能会让那些在更强大的免疫系统中【编注:为防止疾病,密集的速生鸡群需要不断地摄入激素、抗生素等】存活的病原体胜出。延长活体动物贸易和出口的地理范围,增加了相关病原体可交换基因组片段的多样性,提高了疾病因子探索其进化可能性的速度。
生态养殖
美国北卡的工业化养殖鸡场
尽管病原体以不同的方式迅速进化,它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有效干预(即使有效干预能够让人们挽救一季度的财政收入)。目前的趋势是这样的:政府减少对农场和加工厂的检查;通过立法来反对政府的监管和反对社会活动家的曝光;甚至立法反对媒体披露疫情爆发的细节。尽管最近法院对农药和生猪污染进行了裁决,但私人生产仍然利润为先。美国的当务之急却是把疫情爆发所造成的破坏外在化(externalized),到牲畜、农作物、野生动植物、工人、地方政府、国外政府、公共卫生系统以及国外的替代农业系统。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报告,食源性疾病正在波及更多的州,影响更多的受感染的人群。
也就是说,资本产生的异化有利于病原体的传播。当公众利益被农场和食品工厂所拒之门外,病原体则穿透了产业不愿意承担的生物安全。日常的工业生产代表了一种唯利是图的道德风险,蚕食我们共享的健康共同体(health commons)。
5、敢问解放之路在何方?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纽约,和病毒最初的爆发城市隔着一个半球。在纽约,有一个巨大的反讽:数以百万计的纽约人住在由前不久还担任纽约市副市长艾丽西亚·格伦(Alicia Glen)所监管的住房里躲避着灾祸。格伦直到2018年还是纽约市主管住房和经济发展的副市长。她的另一个身份是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前高管,格伦负责监理城市投资集团(UIG),负责开发那些被这一集团其他部门限制贷款的区域。
当然,格伦个人并不能为这次疫情的爆发负责,她更多的是一个象征,说明疫情已经在叩门了。在进入纽约市政工作的三年前,纽约出现住房危机和经济大萧条(部分原因是自作自受),她的前雇主与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一起获得了联邦政府63%的紧急贷款。高盛不仅摆脱了日常管理费用,还在危机中开始分散投资。它购入了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的股份。双汇是中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一部分,它收购的美国史密斯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商。高盛还以3亿美元的价格获得福建和湖南的十个家禽养殖场的所有权。湖南和福建距离武汉最多只有一省之隔,而且也都恰好在该市的野生动物流域。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一起,高盛又投资了3亿美元,在两个省发展养猪业。
上面对于“关联性地理”的探讨回到美国也同样适用。目前,大流行病侵袭着纽约格伦选区的一间间公寓,使得其成为整个美国最大的新冠病毒的传染地。我们可能还需要承认,尽管高盛的投资对于中国农业系统的规模而言并不算太大,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纽约可以算是疫情爆发的因果链上的起点。
民族主义式的指责不仅体现在特朗普将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而且也有整个自由主义谱系的参与。这种指责实际上掩盖了相互关联的全球国家和城市。卡尔·马克思曾用“敌人兄弟”描述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劳动人民在战场上、经济上遭受着伤害与死亡,如今在自己的沙发上苟延残喘,奋力求生。这些显示出了精英人士之间为争夺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竞争,也体现他们在分裂和征服人性的手段上的相似性。
确实,一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流行病,可以使得该系统的管理者和受益者在另一方面收益颇丰。2月中旬,五名美国参议员和二十名众议院议员倾销了数百万美元的股票。尽管一些议员公开重申没有内部情报交换,但这些政客已经根据知情者的机密情报做出了行动。
在如此残酷的掠夺之外,美国国内的腐败也是系统性的。资本套现,也标志着美国积累周期的终结。
现实中,维持资本运作的工作仍在继续,资本的运作甚至围绕生态(和相关流行病学)展开。这次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于高盛本身来说,像以前的危机一样,提供了“增长空间”:
基于迄今为止在各种疗法和疫苗上取得的良好进展,我们与生物技术公司的各种疫苗专家和研究人员一样乐观。我们相信,一旦有这种进步的重要证据出现,人们的恐惧将会消失......
当年终目标大幅提高时,在可能的支撑位入场交易的尝试只适合日间交易者、趋势追随者和某些对冲基金经理,但不适用于长期投资者。同样重要的是,以市场达到低位作为今天就卖出的理由,也是没有任何保证的。相反地,鉴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和优越性,我们比较有信心市场最终将达到预期高位。
最后,我们实际上认为当前市场为缓慢增加投资组合风险水平提供了好的时机。对于那些拥有闲置资金,并在正确的战略资产配置上具有持久力的人来说,这是开始逐步增持标准普尔股票的时候了。
由于对疫病持续吞噬生命的恐惧,世界各地的人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资本和工业生产的循环是罪魁祸首;在这次疫情中,这个循环像是被病原体放射性标记了一样,留下一个接一个的行径记号。
那么如何不局限于那些偶发的和不确凿的事件,来准确形容此类系统?我们的小组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模型,该模型试图超越了之前一些理论,包括生态健康 (ecohealth) 和“一健康 (One Health)”理论中的的现代殖民医学(modern colonial medicine)---它继续将森林砍伐这一导致致命疾病出现的源头归咎于土著和地方小农。
我们关于新自由主义式疾病出现的一般理论结合了:
全球资本的循环;
资本运作所导致的对能够阻止病原体扩散的区域环境复杂性的破坏;
病原体溢出事件的发生率和分类复杂程度的增加;
不断扩大的城乡结合部的商品交易:它们将这些新溢出的牲畜和劳动力携带的病原体从最深的腹地运送到区域性大城市;
日益增长的全球旅行(和牲畜贸易)网络:它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将病原体从上述城市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这些网络如何降低传播摩擦(transmission friction),为牲畜和人类中更高的病原体致死率的自然选择进化铺路;
以及,除已有的强制之外,工业化养殖中,极度缺乏自然繁殖(reproduction on-site):这就剥夺了生态系统免费提供的、天然且实时的防病抗病服务:自然选择。
这一理论应用的前提是,COVID-19和其他此类病原体的成因不仅仅在病原体感染目标或其临床过程中发现,而是也出现在生态系统关系领域,这领域已经被资本和其他结构性因素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所掌控。每次有病原体大爆发,都有代表不同的分类单元、来源宿主、传播方式、临床病程和流行病学结果的丰富多样性,让我们目不暇接,而这一切又恰巧标示出与土地使用和价值积累完全一致的路径。
通用的干预程序,是可以对多种病毒同时产生作用,从而远远超出了某种特定病毒的范围。
为了避免出现最糟糕的结果,下一个人类的重大转折应该是“去异化”(disalienation):放弃定居者的意识形态【编注:此处应指白人从欧洲到美洲、大洋洲的殖民定居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将人类重新带入地球的再生循环,并在国家和资本领域以外的众多层面重新发现我们的个体意识。经济主义(economism),这个将一切都归因于经济的信仰,还是不足以解放我们。全球资本主义像是古希腊神话中有多头的水蛇怪(Hydra),它会挪用、内化和安排多层次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会在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复杂且相互联系的领域中运作,不断地构建起当地的价值体系。
历史学家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曾经批评所谓的“救赎历史”(salvation history)。不过,在病毒的问题上,我们可能要重提这个带有救赎历史性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及时拆掉定时炸弹吗?”去异化就是要去除在资本积累中各个层次的、各种方式的压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去除资本在生产、社会和符号领域的占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走出资本的极权。资本主义使一切事物商品化:不仅是工厂和农场,商品化也出现在火星探测、睡眠、锂储量丰富的泻湖、呼吸机的维修,甚至可持续发展,凡此种种。普天下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市场的影响,特别在此次疫情中,市场被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以拟人化的方式凸显出来。
简而言之,无论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步兵”(包括前文的格伦)如何试图调和冲突,一切能成功阻止农业经济圈中病原体大规模杀伤人类的干预措施,都必须与全球资本及其地方代表的进行对决。正如我们小组在一些最新工作中所描述的那样,商业化农业(agribusiness)与公共卫生处于战争之中。而公共卫生处于下风。
但是,如果人类文明赢得了这次百年一遇的冲突,我们可以将自己重新带入一种全世界共享的、可以重新连接我们的生态和经济的新陈代谢系统中。这样的理想不仅仅是乌托邦式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收集即时的解决方案。我们保护森林的复杂性,使致命的病原体不会将宿主连接起来,而直接攻击全世界的旅行网络。我们重新引入牲畜和农作物的多样性,并以一定规模重新整合动物养殖和农作物种植,以防止病原体在毒力提升以及防止在地理范围内扩散。我们允许牲畜自由繁殖,重新开始自然选择,使免疫体系进化到能够实时跟踪病原体。总体上,我们不再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区,作为市场竞争中的对手。
出路在哪里呢,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或者也许是回归到世界本身)。这才能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从纽约到北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困在客厅,或更不幸地正在悼念死者,都不会想再次经历类似的疫情爆发。是的,传染病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导致过早死亡的因素,仍然是一个威胁。但是,鉴于目前充满兽性的病原体正在肆虐,而且每年都会发生病毒的“溢出事件”,在比1918年【编注: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导致全球5亿人患病,数千万人死亡】以来的百年间隔更短的时间内,我们很可能面临另一场致命的大流行。我们能否从根本上调整我们利用自然界的方式,与此类传染病休战?
注释:
[1]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发现,武汉的第一个病例和第一批7位病人中的五位,都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研究者们认为病毒可能在11月就已经出现在武汉,病毒可能是从外面带入华南海鲜市场,然后通过市场扩散的。Huang Chaolin, et al. 2020.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The Lancet 395, no. 10223 (Jan. 24, 2020): 497-506.Yu Wen-Bin, “Decoding Evolution and Transmissions of Novel Pneumonia Coronavirus Using the Whole Genomic Data,” ChinaXiv.org, Feb. 21, 2020, www.chinaxiv.org/abs/202002.00033. Daniel Lucey, 美国Georgetown University传染病学专家说,“病毒先进入那个市场,然后又从那里出来。” 参见Jon Cohen, “Wuhan Seafood Market May Not be Source of Novel Virus Spreading Globally,” Science, Jan. 26, 2020; “Coronavirus did not Originate in Wuhan Seafood Market, Chinese Scientists Say,” SCMP, Feb. 24, 2020。Peter Daszak, 人畜共患病毒专家,美国EcoHealth Alliance的负责人,认为“大家都假设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起源地。但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in the US, observed that “Everybody’s assuming … that market was the origin. We don’t know that. Helen Branwell, “Chinese Scientists Obtain Genetic Sequence of Mysterious Virus, a Key Step in Containment Efforts,” Stat, Jan. 9, 2020, www.statnews.com/2020/01/09/chinese-scientists-obtain-genetic-sequence-of-mysterious-virus-a-key-step-in-containment-effo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