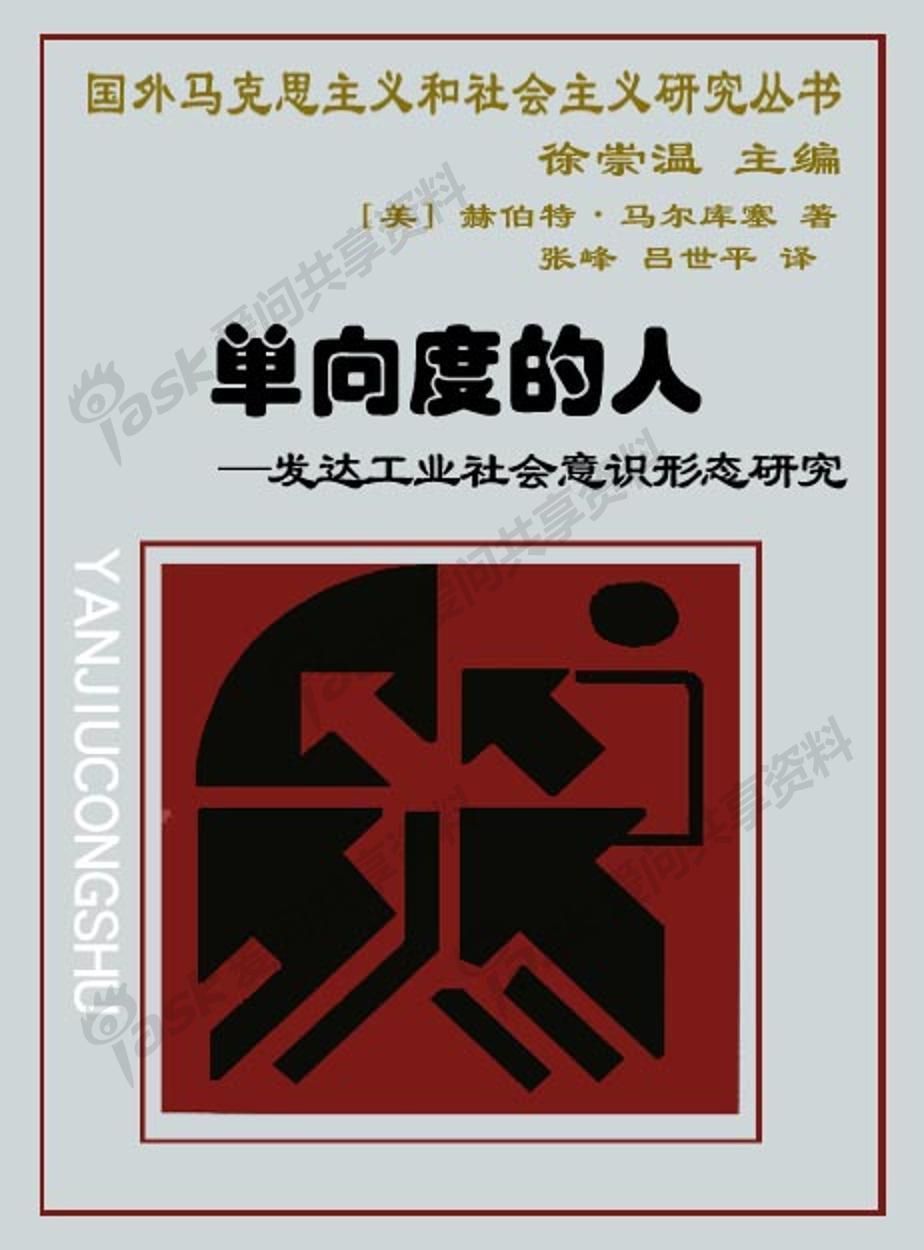老田 |《无依之地》:赵婷导演的底层自我意义生产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21-03-11 阅读:1553 次
导语
关于《无依之地》的导演赵婷,社交媒体的舆论出现了戏剧性的大转折,从“中国的骄傲”变成了“辱华”(具体请看今天推送的第二、第三篇文章),目前《无依之地》暂停公映。本次食物君推送三篇评论,从不同视角提供分析,以飨读者。
老田把《无依之地》放置于意识形态生产的历史场景中。随着新自由主义消解“福利国家”,制造业外迁,贫富分化加速,贫穷在美国迅速弥漫,灯塔国也开始面临“良性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赤字。如何讲述穷人,给无依无靠的底层流浪者创造出自我价值感、获得感,这是《无依之地》的艺术成就,也是讲好美国故事的意识形态成就。
林一五的评论“谁的无依之地?”,从原著到电影,从作者到导演,抽丝剥茧,指出了电影也算上乘之作,然而“归根结底,······底色是城市精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记录穷人们的生活,念念不忘的大多是穷人们对她‘真实描绘他们尊严’的感谢,以及对‘人们拥有如此之强适应力’的赏玩。”
郭松民认为,对赵婷导演,无论是前些时候兴高采烈的“拉”,还是突然而至的“踩”,都是用力过度,体现了不自信。更重要的是,赵婷谈论中国的观点并不鲜见,前几年在中国也算主流,目前“仅仅是受到了一定压制,但并没有受到系统的批判和清理,也没有新的历史叙述、政治叙述和理论叙述能够取代它们,这才是最严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老田
责编 | 侯解、侯怡
后台编辑|童话
图片来源:网络
赵导演倒不是满口谎言,她们在创造,给无依无靠的底层流浪者创造出自我价值感、获得感,啊,多么伟大的美国艺术家们!
毕竟,马克斯·韦伯不是说过了么:人是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有意义的人生,哪怕穷点苦点,也更加容易忍受些。不是老有人在耳边提醒我们么:别光看眼前的苟且,还得想想诗和远方么。
在给意义网络赋值方面,赵导演还是做得不错的。跟好莱坞名角和导演安吉莉拉·朱莉相比,赵导演胜出多多。下左图是赵导演选择的自我意义生产模特,及其对人生意义的阐述——具有天人合一的高度和体悟,显然,比安吉莉拉在伊拉克废墟上的讲述(右图),更能够吸引人。这就说明了,同属于意义网络的编织工作,其间是有高低差别的,朱莉那时那地的讲述,就显得极其干瘪,缺乏进行完美赋值的想象力空间。【编者注:下两图均引自林一五文章:《谁的无依之地:从赵婷到布鲁德》,公众号“ 林一五议时”,见今天推送的第二篇】
左图:赵导演拍摄的银幕故事讲述者,穷人如何在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具体而真切地看到了诗和远方;右图:身穿防弹衣、被美国大兵保护着、站在伊拉克的残垣断壁间的安吉丽娜·朱莉(号称“好莱坞最性感女神”),她说:“虽然他们(伊拉克难民)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直接用民主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去替代无家可归者的需求满足层次,显属于意识形态宣传干事的活路,不是导演和演员的职业本分——而讲一个具有可信度的好故事,才是演职员的本分。按照足球场上的规矩,朱莉那么干,属于严重的“越位”犯规行为,而赵导演就不是那样。
要是有了此种自我意义生产之后,穷人再也感觉不到苦、累和绝望,那个虚拟赋值工作,就真的无所不能了。看来这个很难,如同朋友所言:“虚拟赋值是一个意识形态工作,主要用来感动或说服小资,如果小资们脱离历史、脱离底层的生活敏感,是容易被感动和说服的。”
这么一来,虚拟意义赋值工作的成功,还得利用一下“主体间性”——拿甲方的苦难和绝望,在乙方的头脑里完成虚拟赋值——这个意识形态的效果还是有点“隔”,看来只能够起到类似于“有色眼镜”的作用。
二战后,马尔库塞等人痛感西方的工人阶级也往往不提出革命要求,安于工人贵族地位,还接受了各种单向度思维。那种状况今天去回顾,大概属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劳动阶级充分而有效,其统治合法性得到了来自马克思命名的革命阶级的赞同,这可能属于“合法性黑字”【编者注:此处借用了财政术语,赤字指支出比收入多,黑字则指收入比支出多】状况——统治者实现了对潜在革命者的高度同化效果。
图片来源:网络
等到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启,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外移,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大批绝对受损者阶层,工人贵族地位由此一去不返,这就出现了各种需要处置的“合法性赤字”状况。特朗普的各种对外的强硬攻击性,无非是要对内虚拟构建一种基于“劳动力行会”的想象力,去对接与合法性赤字有关的阶层痛感;特朗普的选战策略,作为一种“成功的”策略还支持了选战胜出,这说明在美国社会中间,透过上下层之间的选举互动,就此形成了一种彼此接受的共识或者博弈均衡。就这样,美国政客以极端的对外非议,去转化内部的合法性赤字,这个也属于意识形态生产策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赵导演的《无依之地》,故事及其脉络都未必是假的,有些底层人士往往也进行自我意义生产或者虚拟赋值,如同民间歇后语所言“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如果小说作者找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其实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虚构一个出来),而导演又以新的媒介方式,在不同的思想空间里,去表现和传播这一个“自我安抚与麻醉”的自我意义生产方式;显然,这同样有助于填补美国的“合法性赤字”,从而在人们的自我心理空间里,透过自我意义生产去完成填补亏空的工作。据说,为了深化主题,导演还安排了主人公拒绝脱离流浪生涯的天赐机会,似乎,流浪路上别具人生意义还难于割舍,并不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绝望选择,这么一来,女主就好像有点美版的、高档的“三和大神”的味道了。
既然造成合法性赤字的相关问题,在真实世界里无法解决,那么,对外转嫁或者向内转化,都是意识形态赋值努力的重要方面。显然,这个并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那么从心理上缓解或者转化相关问题,使其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就算是有了,所以“转化或者缓解痛苦”就成了意识形态经营的重点攻关方向。舍此之外,还有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人所说的“奶头乐”战略等方式,那个方向可能适合于年轻人。而但对于欲望递减的老年人来说,赵导演的表现努力,可能更适合一些——这显属“更健康”的“正能量”虚拟赋值方向。
在填补合法性赤字方面,赵导演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而且,在表现手法上较之安吉莉拉·朱莉更为圆满自洽,当然也可能具有更高的“潜在市场价值”——裹挟更多的头脑和人。从特朗普的对外攻击性的转化策略,到奶头乐的欲望与情绪转化努力,再加上赵导演们的自我意义生产构建,这些多层次努力,看起来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细分市场”策略——对外强硬攻击适合于死抱住“工人贵族梦想”不放的群体,而奶头乐战略可能更适合于年轻人,但自我意义赋值则明显更适合老年人了。所以,在意识形态生产领域,千万别拿导演不当干部,自我意义生产的转化能力,不见得比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效果更差些。
一个反华崇美的赵导演去拍摄这样的片子,可能还具有近似于中国某些人的“慕洋犬”心理那种“修辞作用”——你看洋人都说好了,那更可能是真的好。
记得1980年代,河shang派(自由派与公知的鼻祖)往往宣传西方的富裕发达,以诱惑中国民众,说只要是搞了资本主义的蔚蓝色文明,大伙儿都可以指望跟美国的蓝领工人贵族那样:一个人上班养活老婆孩子不说,还有房有车。还真的别说,富裕发达就是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大伙儿中间被说服的还不少,真有不少了开始拥护走资反社了。怎么到了新世纪之后还没有过多久,其精神后裔如赵导演,就转而宣传美国穷人开始了自我意义生产,由此克服了眼前的苟且,并成功地望见了诗和远方呢?
感觉,美国和西方作为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资源,似乎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换:从前河shang派往往透过“硬指标”宣传其制度优越性,现在,河shang派的精神后裔,全盘抛弃“硬指标”不说,还开始了“软指标”和意义网络构建的推销技术,这个转换幅度太大,弯子也转得有点太急了。当然,有思想准备的人还是有的,赵导演讲述的美国故事,就很受国内南方系媒体的期待。难道,河shang派宣传的那种“硬指标”的意识形态产能,这么快都已经挖掘殆尽了吗?需要实现由赵导演代表的、这么大幅度的意识形态策略转型?目前还不知道,这个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公知们多年来推销的“西方好资本主义”梦想,此后是否需要彻底更换其卖点。
反过来,赵导演在美国获奖,虽然不一定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功,但确实体现了全球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某种新特点或者共性;作为盛世中国的表现之一,在中西方相对落差的中国形象,似乎在西方也日益成为最具有意识形态产能的生长点。
庚子年疫情暴起,CNN和BBC等往往不得不系统地发布谎言以冒充事实,然后去裹挟西方民众,目的不言而喻——他们对于弥补合法性赤字方面的亏空,也担负有自觉责任,要不然为什么硬是要说谎?难道脸皮(商誉)真的不值钱了么?要知道说谎对于新闻机构的潜在损害,可能要大很多很多倍,这么干完全是高度责任心驱使的结果。而赵导演就无需“卖脸皮”,她透过复述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就达成了差不多的目的,与CNN和BBC一对照,就分出了职业方向选择的高下。
此外,赵导演的成功,也还有点别的味道在。感觉从新世纪开始,原产中国的人士在填补西方的“合法性赤字”方面别具格位——填补西方国家的合法性赤字方面独具生产性——甚至还在西方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江湖地位和虚拟价值都一路看涨了,这似乎不算是一件完全的坏事:这至少说明西方国家也感到不可能关起门来完成内部意识形态生产目标了。
有这么几件事值得提到,新世纪初年,张戎以滥书【编者注:Mao: the Unknown Story, 2005年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一炮走红,激发了中国多少公知和自由派的光荣与梦想;然后杨继绳的行情看涨(一切成功都会引起模仿,港大历史系的冯克教授就近乎精准抄袭杨继绳的讲故事方式),最近的成功者是武汉的汪主席。这些人都是以原产于中国的身份,在中西对照的视野里否定中国,或者以各种方式申说资本主义之外的制度实践无效甚或有害,这就有力地呼应了撒切尔那个著名的论断——“别无选择”。似乎,他们的中国人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市场上的卖点或说服力,然后再叠加各种“现身说法”去讲述“西方好抑或中国糟”,这对于西方受众而言,无疑多了那么一丢丢可信度,这两者都成为意识形态经营的修辞力量源泉。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