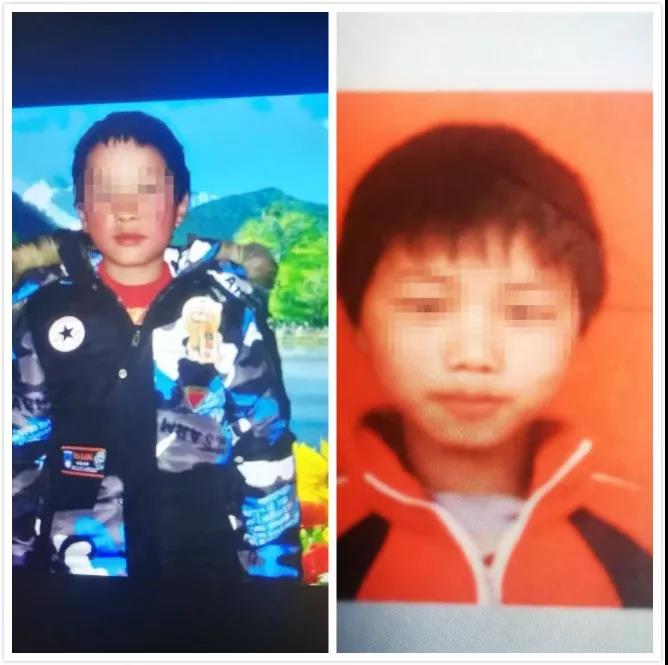兄弟俩放牛不幸被垃圾掩埋双双送命:哥哥12岁,弟弟10岁
来源: 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8-07-21 阅读:3026 次
堆积成山的垃圾|受访者供图
7月13日上午,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花山乡花山村燃起送葬的爆竹和烟花。
逝者是周家的兄弟俩,哥哥12岁,小学五年级;弟弟10岁,小学三年级。三天前,两人到垃圾场旁的山坡上放牛时失踪;两天后,遗体被从垮塌的垃圾里找到,已无生命体征。
吞没兄弟俩的垃圾场位于村东山坳,天然形成的坑里堆着整个乡镇10年左右的垃圾,因体量巨大,村民称之为“垃圾山”。
在村民印象中,“垃圾山”无人看管、没有护栏,里面的垃圾未经任何处理。而在雨水浸泡及自身重力下,“垃圾山”此前曾发生过规模不一的十余次垮塌,都未被视为隐患。
直到悲剧从天而降。
云南昭通遭垃圾山掩埋两儿童确认死亡,遗体已被找到|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儿子找不到了”
从昭通市镇雄县出发,沿着302省道走上80多公里,就到了花山村。
路是盘山路。车子来来回回地绕,绕过连绵的梯田和玉米地,马路另一侧的山谷越来越深。农户的白房子散落在地势平坦的地方。
资料显示,镇雄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云南人口和农业人口最多的县;花山村是它200多个下辖村之一,和许多村落别无二致:海拔高,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进村的水泥路是几年前才修好的,耕地不多,没有大型工厂,青壮年以外出务工为主。
在周家,父亲周高成在四川的建筑工地打工,母亲吴学敏在家务农、照顾小孩。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两个女儿读初中,两个儿子读小学。
最小的儿子出生前,吴学敏也在外打工,从浙江到江西,三个孩子带在身边。2009年小儿子出生后,吴学敏回到故乡,“在我们农村,两个儿子就享到福了嘛。”
7月10日晚,太阳从云贵高原的山野里滑走。吴学敏把一盘炒土豆、一碟花豆、一碗酸汤摆上桌,等两个放牛的儿子回家吃饭。
六点多,自家的两头牛跟着别人家的牛群一起回了村,但儿子迟迟未归。
吴学敏有些急,开始给儿子的同学和朋友家打电话,“打是打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儿从来不会到哪家去。”她又到村里村外走了一遭,还是没找到。
七点左右,她给在四川打工的丈夫周高成打电话,告知“儿子找不到了”。周高成报了警,随后搭上赶往老家的车;吴学敏则叫上同村的亲戚邻居,四下寻找。
有关两个孩子的讯息零零散散传到吴学敏耳朵里,孩子的姑奶奶说,下午三点多,她发现孩子放牛附近的垃圾山发生过垮塌;同村的村民说,当天曾看到过两个小孩在垃圾山附近玩。
两个消息撞在一起,人们开始将焦点锁定垃圾山。
7月11日早上,家人和村民在垃圾山挖掘,搜寻两个失踪小孩|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防火、防雷,没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挖掘从11日清早开始。
周家亲戚和村民一开始用锄头和铁锨在垃圾堆进行挖掘。
塑料袋、旧衣服棉被和煤炭残渣裹在一起,“根本拽不出来”;盛夏季节,一铁锨下去,垃圾的腐臭味直接扑在脸上,招来嗡嗡的苍蝇。每个挖掘者都戴着两层以上口罩,隔上十几分钟换一批人。
此后,政府从建筑工地临时借调过来的挖掘机器到场。
在挖掘现场的村民见证,“12号中午11点多,挖到了弟弟,又一个小时左右,挖到了哥哥。”
现场医疗组确认,两名儿童已无生命体征。
在村民们眼里,这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在当时,对两个小孩子来说,大堆垃圾从天而降,即便具备自救能力,也根本没有机会;就算呼救,但垃圾场距离村子一两公里,也不会被人听到;垃圾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但变电站里就算有人值班,能听到的也只是机器的轰鸣……
“谁能想得到呢。”人们叹气。
7月13日,乡政府以“给他们一些关心,让他们建立对生活的信心”的名义,为周家提供补助31.8万。同一天,两位少年下葬。
事后,回忆起两个年轻生命,亲戚朋友无一例外地给出“乖巧”“懂事”“听话”等词,他们主动做家务,不和同龄人打架,也曾经在老师眼里“不注重个人卫生,有些调皮捣蛋”。
回忆起事情的经过,家人总觉得有无数种可能让两个孩子躲过这场灾难——
兄弟俩就读的小学,7月8日开始放暑假。家长有繁重的农活要做,放牛通常是农村小孩子的假期任务。“还不如不放假呢,就不会出事了。”孩子的堂哥说。
在“365天中有200天会下雨”的镇雄,7月的雨更是说下就下,事发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事发后,又接连下了两场雨。唯独10号那天,天晴,还出了太阳。“要是下雨就好了,他们就不去(放牛)了。”孩子的表舅说。
以往,同村的两个小孩喜欢到周家找兄弟俩玩,然后四个人一起去放牛,那天他们却迟迟没去,俩兄弟没继续等,赶着牛出发了。“要是一起去,出事还有个喊‘救命’的。”孩子的母亲说。
但偏偏每一种假设都没有发生。
左为弟弟,10岁,小学三年级毕业;右为哥哥,12岁,小学五年级毕业|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也有村民开始反思对孩子安全教育上的缺失。
一位村干部介绍,花山村的海拔大约2000米左右,山多,耕地少,农作物主要生产苞谷、洋芋和苦荞。“苦荞几块钱一斤,洋芋八角,苞谷五角,收个几千斤,一年到头根本赚不到多少钱。”
所以,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下照顾小孩;夫妻外出打工,老人照顾小孩;或是托付给亲戚照看。有村民调侃:“我们这里过节只过六一、三八、九九——儿童节、妇女节、老人节。”
在村民们眼里,在房顶上蒙着眼睛捉迷藏,用苞谷秆搭成小房子,坐在里面点火玩,这些几乎是当地每个小男孩共同的经历。父母无法随时在身旁看管,自身又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这样的情况一度让作为老师的赵敏觉得头疼:
农村留守儿童多,家长们要么没有精力管小孩子,要么安全意识薄弱。你老是说孩子们不要在公路上骑自行车了,但是家长还是会买给他;我们在班会课上说了放学回家不要去采野果、野生菌,去了家长也不管;开家长会了在黑板上多讲几句,他们觉得自己的时间太宝贵了……
被教育过防火、防雷、防溺水的两个男孩,最终没防住垮塌的垃圾山。
垃圾山
村民口中的垃圾山,位于花山村东侧两公里处的山坳,垃圾在天然形成的坑中堆成山形,从上俯视,垃圾山和普通操场面积相当。有人估计,“得有四五十米高。”
花山村是花山乡的政府所在地,有村干部和村民证实,这座位于花山村的垃圾场除了容纳本村的垃圾,也将花山镇上的垃圾收入其中。
一位村干部介绍,花山乡下辖六个村,共有3万人口,其中镇上人口有1万。在镇上,商铺和住宅分布在一段2公里左右的主街两侧。
花白头发的老蒋是花山乡的垃圾车司机,从2010年2月以来,他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开始工作,将垃圾车的音乐打开,沿着主街缓缓而行,居民们听到音乐声,便带着垃圾出门,丢进绿色车斗里。
村民们放在路边准备倾倒进垃圾车的垃圾|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镇上的垃圾大概在两三个小时后敛收完毕,老蒋把车开到垃圾场,倾倒下去,中午12点前完成一天的工作。
事发当天,老蒋在上午11点多倒完垃圾,他回忆,那时的垃圾山没什么异样。直到晚上八九点,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叫他过去看,他向在场的村民证实:“垮了。”
老蒋说,“时间长了,有淤泥,还被水泡着,和上面的垃圾一起垮下来了。”
在村民的记忆里,这个垃圾山“有些年头了”。有人说五六年,有人说至少九年,也有人说十五六年。老蒋最肯定:“快11年了。”
村民们都说,这期间,垃圾场无人看管、没有护栏,里面的垃圾未经任何处理。
老蒋说:“五年前有标志牌的,写着‘垃圾场,禁止入内’,时间长了就没有了,又没人经管,标志牌就丢掉了。”
花山村一位村干部说:“我们还算不错的,是有地方倒垃圾,好多地方都没有地方倒。有的村都是就地掩埋,我们是垃圾处理比较好的,有集中堆放点。”
事发后,镇雄县委宣传部外宣部主任熊涛说:“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很多问题都暂时没办法解决……我们县里面都没有处置垃圾的能力。”
花山村村干部介绍,垃圾山所在的土地,是村集体的,两侧山坡上的草丰厚肥美,是村民们放牛放羊的地方。有时候小孩子放牧无聊,便会到垃圾堆里翻找玩具。
有村民曾看到过,有小孩在里面捡到四五十公分长的胶质玩具马,还有的捡到过小低音炮,“修了修还能用”。成年人偶尔也会去,“在里面捡瓶瓶罐罐卖废品,听说还有人捡到过钱。”
垃圾场旁是花山村集体所有的草场,村民们通常来这里放牛|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出事前,没有人把它当成安全隐患。
很多村民都知道,7月10日的垮塌并非是垃圾山多年来的第一次垮塌,就在一个月前便有过一次。
“一开始有点斜。”老蒋用手比了一个75度左右的斜坡,“农历的五月初三(6月16日)晚上垮掉一次,下雨,垮下去上千方(立方米)”——老蒋所驾驶的垃圾车,一车的容量大概有七八方。
多位村民证实,那一次的垮塌后,原本有坡度的垃圾山变成了直上直下的形状,垮掉的垃圾向天坑更深处摊开,剩下的部分变成了断崖,“上面有一个洼(凹陷进去的地方)”。
7月10日,在连续几天的暴雨冲击后,垃圾山再次发生垮塌,上面的垃圾倾泻而下,和一个月前的垮塌相比,这一次的规模不大,“200方左右”,但恰巧,将两个孩子掩埋其中。
倒着倒着,就形成了一个山
垃圾山,对昭通而言并不陌生。
一个月前的6月13日,昭通在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期间被通报批评,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称:
云南省昭通市至今尚未建成规范化垃圾处理设施,这在全国地级市极为少见。由于长期缺乏规范的垃圾填埋场,全市垃圾污染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清华大学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介绍,类似的“垃圾山”现象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比较常见:
它其实没有什么规划,可能有矿坑啊、采石场啊,稍微偏僻的地方,刚开始这个地方开始堆了,慢慢的大家就把垃圾倒在这里,倒着倒着,就形成了一个山。
他总结,农村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会释放出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有的东西腐烂、降解,产生一些废水渗入到地下,污染地下水和土壤;臭气散发到空气当中,就是空气污染物。有的地方垃圾堆放到一段时间,点一把火露天焚烧,这对空气的危害更大;而且垃圾中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比如废弃的农药,这些东西的污染也更严重。”
垃圾车司机老蒋每天收集镇上的垃圾,倾倒进垃圾场|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但恰恰,花山村的垃圾山在东边的山谷里,与村落相隔一两公里和一个小山包,距离和几十米深的天然坑阻挡了垃圾腐臭的传播;垃圾山附近的山坡是花山村的集体草场,没有农田,垃圾不影响农业生产;当地的喀斯特地貌无法储存降水,村民通常饮用山泉水,所以被垃圾污染的地下水也并不影响生活。
它几乎避开了全部作为环境问题而引发关注的点,但在被忽视十余年后,作为安全问题一下爆发。
事实上,此类垃圾山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并非孤例,据媒体报道,2007年9月,石狮市石狮南环路湖滨与灵秀镇交界处,一座垃圾山突然塌方,住在山下临时搭盖房的一家三口遇难;2011年5月,太原市东坪村一垃圾消纳场发生垃圾滑落,造成当地两名拾荒者死亡;2012年9月,兰州市寺儿沟垃圾填埋场发生垃圾倒塌,一外地拾荒男子被掩埋;2015年12月,深圳光明新区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的受纳场垮塌,造成73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
刘建国说,农村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交通比较便利、村庄人口聚集度较高的地方,例如长三角和华北地区,主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方式处理,村收集、乡镇运输、区县处理;而在经济和交通相对落后、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主要通过较为原始的方式处理,例如露天堆放、用土掩埋等,“基本上属于没有管理的一种状态。”
他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村垃圾治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讲是两重天。城市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民生公益保障事业来做,政府财政出资,形成专业化的队伍,建设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一枝独秀;但农村就非常的薄弱,没有资金,没有队伍,没有设施,三无的情况下,当然会导致垃圾成山。
最近几天,花山乡的垃圾场旁正在修建围墙,新设的蓝色警示牌立在一侧,写着:此处危险,禁止入内。镇雄县政府新闻办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等我们的垃圾发电厂建成以后,我们就会把这些垃圾全部进行清理。”
最近几天,花山乡的垃圾场旁正在修建围墙|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关于垃圾山由哪个部门管理,发电厂建在哪里,如今建设到什么程度、日后的垃圾如何处理等问题,镇雄县官方并未回复。镇雄县外宣部主任熊涛表示,不对此事相关的话题再做回应,“除了聊工作,其他都可以聊。”
记者查询,7月4日搜狐网财经频道曾发文称,7月2日,云南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镇雄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相关工作。会议强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镇雄县城镇化发展中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难题的现实需要,是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迫切需求。要尽快科学合理制定招标方案,让真正有实力、真干实干的投资商投资建设,确保项目能真正落地。
7月15日,周家兄弟下葬的第三天,也是花山乡的集市。小商贩在马路两旁支起红色帐篷,售卖水果、日用百货。吴学敏从山坡上的家中下来,把两个儿子的寿衣钱,结算给镇上的布店老板。
下午一点多,垃圾车司机老蒋戴着他的红帽子上车。
两个多小时后,一条街的垃圾收入车中。他照例把车开到垃圾山旁,按下按钮,七八方垃圾倾泻而下。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原标题:《夺命垃圾山:两位农村少年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