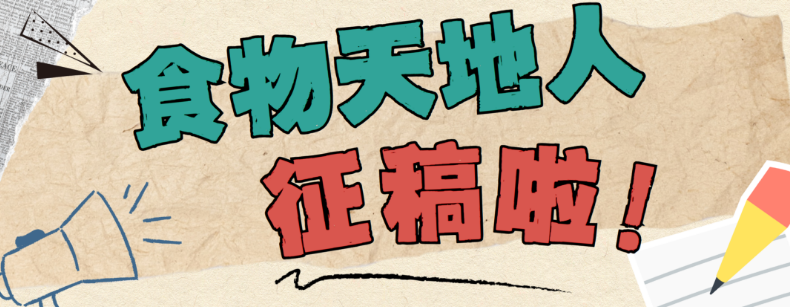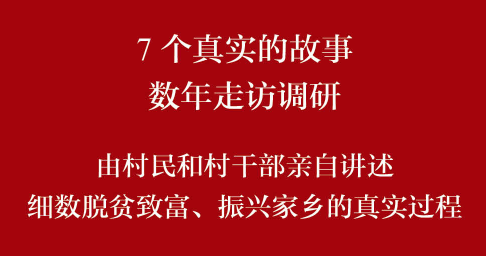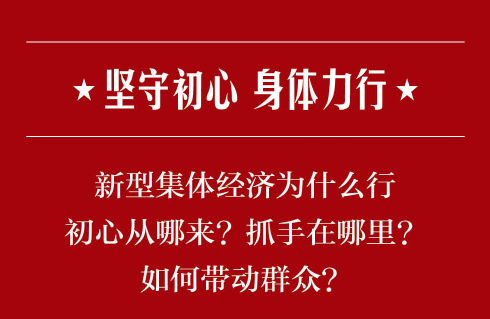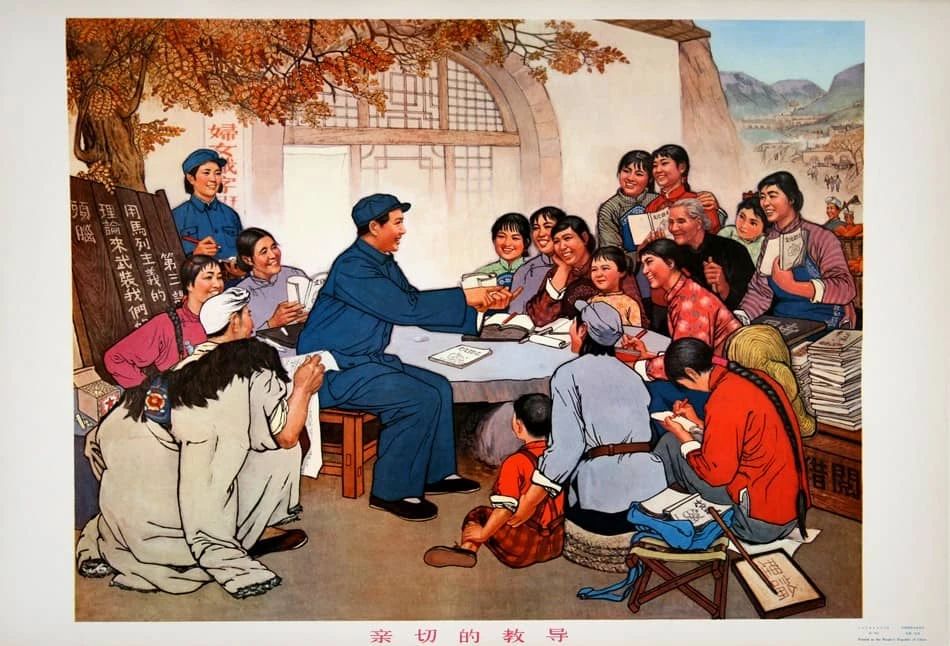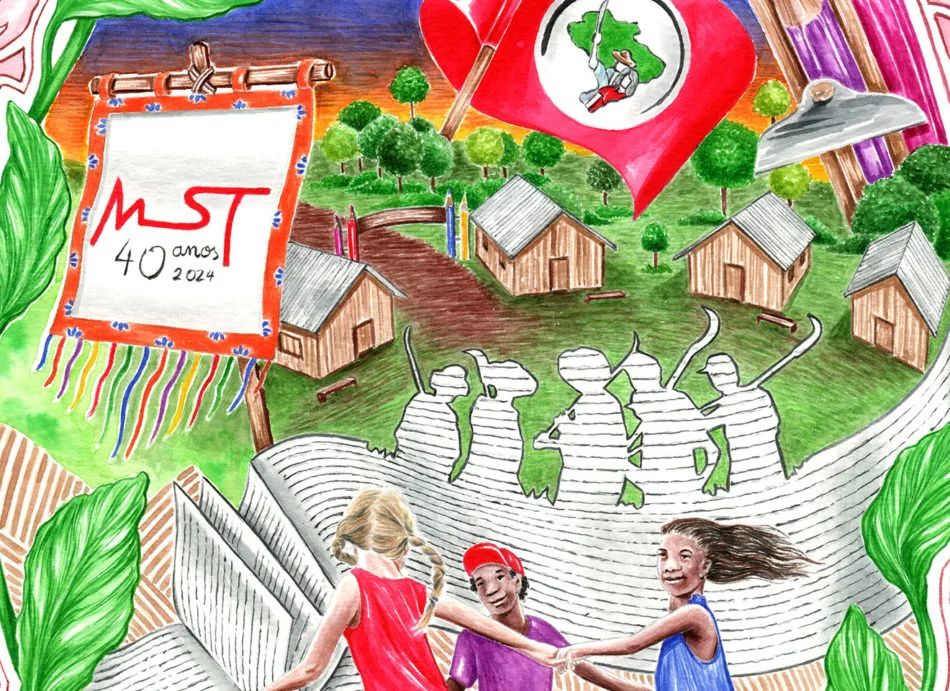诚食谈心 | 博士后回乡种地,她在追求什么?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5-09-19 阅读:560 次
导 语
当小展这位拥有博士后头衔的 “新农人”,在杨陵的土地上为获得五亩试验田的自主管理权欢呼时,她的故事恰是无数生态农人的缩影——怀揣“知行合一”的理想,却深陷现实的重重困局。
化石农业的包围,不确定的土地租期,与合作者的理念分歧,和农场工人的协作难题,养地周期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以及有机认证门槛高、市场定位模糊等困境,几乎囊括了普通人投身生态农业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惑。
但这些难题,并不能否定实践的意义。小展在荒地上铺就喷灌系统、尝试老品种作物、以草养地、做生态科普,每一步,都是在为个人实现生态农业梦而探路。她的摸索,需要时间去检验,但也叩问着这一领域的深层命题:如何突破养地耗时、盈利困难的瓶颈?怎样避免生态成为抬高准入门槛和价格的噱头?
答案或许藏在历史与理论的回响里——从过去农村合作化的经验中汲取集体智慧,以生态社会主义理念为指引,再结合当下每一个“小展”的实践探索,方能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间,为生态农业找到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而这,也正是我们记录这些实践者故事的意义所在。
被访谈者|小展
访谈者&责编|阿大、忍冬
后台排版|童话
“这五亩地要怎么种,我可以说了算了!”电话的那头,一贯波澜不惊的小展,语调里满是兴奋。

划给小展的五亩地最初的样子 | 图片来源:被访谈者供图(下同)
单枪匹马成为一位生态农人的耿小展是有些“耿”在身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专业毕业、中科院生态学博士毕业、德国卡塞尔大学有机农业博士后,博后结束又义无反顾地成为一名生态农业农妇——小展的这份履历显得有些特别。她的博士头衔多少能勾起他人的艳羡,然而,在中国每年递增的博士毕业生中,她也只是十几万分之一,普通的沧海一粟。没有额外社会资源加持的她,与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的农民并无二致。
结束博士后研究项目回国后的小展为什么不去选一个薪资较高的办公室工作,反而去当了生态小农?
一、做生态农业的根是怎么扎下的?
“我想要知行合一,去探索下我学生时代一直只是纸上谈兵的事。”
小展的爱人从事建筑行业。小展说:“以前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天天叭叭地和他说食品安全,他当时就烦了,和我说,你不要光跟我说,你要不然就去实地做”。听了这话,小展心里觉得有道理,以后也很少跟他讲了。
回顾自己硕士时期,当同学们以化学农业管理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小展就已经在做番茄秸秆废弃物的再利用了。当时的小展接触到很多理念,但那会还没有全身投入生态农业的机会,只是小打小闹地做了堆肥,让动物粪便和植物残渣混合,制作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她也在探索一种有意思的植物养分内循环的种植模式,即用番茄秸秆养番茄。当时的小展,结合自己的课题,查阅大量文献,对生态农业的理念和实操比较入迷,也算是为以后做生态农业埋下了种子。
在这期间,因为在农业高校的缘故,身边也接触到搞环保、做生态农场的校友,生态农业的想法,慢慢也就扎下了根。后来考博时又被调剂到生态学,生态农业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根,在小展脑子里扎得更深。博士毕业后小展就在想自己的职业计划与发展方向。她认为,生态农业也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如果这个做不成,也可以再去找其它谋生之路。既然有做生态农业的空间,小展就想去试试,尽力去把生态农业“做起来”。
最终促成小展做出决定的是她硕士导师提供的机会。2016年小展的硕士导师在陕西省杨凌租了50亩地作为教学实践场所。小展夫妻俩与导师一起见过面,她导师邀请小展去杨凌农地创业,并对小展爱人说,“小展如果把事做成了,她的身心状态会比你这个建筑师还要好。”小展爱人也希望看到小展在追求理想中获得价值感,俩人还没有孩子的牵累,所以就支持小展去尝试生态农业了。
“那你父母支持么?”
“我在杨凌,父母亲也管不到我。我读完博后回国,因为疫情在家里待了半年,我妈看我一直在家里待着,就催我赶紧出去工作。如果直接说我是去种地,他们当然一百万个不乐意,但是我就模模糊糊地说,我去杨凌跟着之前的硕士导师创业,他们也就放心了。我父母现在还不用我养,我还可以尝试下追求理想!”
二、生态农业怎样才算“做起来”?——时间成本谁来付?
就这样,投身生态农业的小展,已经在杨凌的土地上耕耘了两年多时间。小展说,时间很宝贵。一是因为,别人投资的是钱,而她投资的是生命,是她最有生命力的几年黄金时间。二是因为,生态农业要养地,而养地所需的时间投入、租地成本、以及个人的生命成本之间形成了不小的张力。
农场是需要效益的,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单从经济上,如果不能持平,是没法产生正面回馈的,如果不能产生收入,很难给这片土地交代,很难给自己交代。毕竟,人活着是需要开支的,现在不用考虑这些,总有未来的万一。然而,在投入生态农业与将生态农业真正做起来之间,还有很多困难和客观限制拦在其间。
首先是大环境给出的限制。农场所处的地址——陕西杨凌,是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辖的唯一县级行政区,它是规模化、工业化、现代化农业的示范窗口。周边的农民能拆迁的都拆了,搬进了杨凌区,土地也都流转出去了。周边各种农业公司承包土地建园区,包括先正达种业,它在杨凌估计有上千亩土地。在化工农业的包围中,小展探索生态农业之路困难重重。
但是,毕竟导师已经承租的50亩地为她提供了尝试的平台。50亩地每年租金5万;导师雇了两位工作人员平时照看土地,人工费用每年共10万左右;除此之外,她导师还建了一个玻璃温室,投入了两百多万。目前,这块地已经投入了约六百万,不需要小展承担。两年多的磨合期,小展与导师磨合,与两位工作人员磨合,与土地磨合,与自己磨合……
小展说,她导师支持她尝试生态农业,但是具体怎么展开,他们俩的想法并不契合。在过去的两年里小展不断修改规划,她对于生态农业的想法是多样化的生态园区,多样化种植,有各种各样的小块田,类似食物森林的状态,配套着研学等。但导师总觉得可行性不强。有机农业的时间线很长,盈利很难,如果把50亩地一下子直接交给小展,导师担心风险太大。
而且,虽说最开始租这50亩地的时候,导师的想法是园区主体不要农药、化肥入场,同时配套用于开展学校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并不指望这块地能产生收益。但是6、7年过去了,随着对土地投入的增加,只投入而不问收益毕竟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也希望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能有些收益,这样才能更可持续。
同时,小展坦言,导师雇佣的两位工作人员对她并不接受,她想尝试的一些耕作方法无法实施。这两位工作人员负责看场地和种麦子、油菜,也种植一些时令蔬果等。50亩地大部分就是小麦和油菜轮种,冬天种小麦或者油菜,5月份收割,6-10月份休耕,等到10、11月份又开始种下一季。曾经尝试过种夏玉米,但因为这里以前是老砖厂,土壤不肥沃,保水性差,浇一次水需要花2000元,后来,就再也没种过。中间留有一点土地给学生做实验。
小展导师要求他们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有虫就让它吃。有牛粪的时候他们就施点粪,长草了就深翻一下。两位长期工有时候就不施肥。毕竟施肥需要人工,他们也不想着投入那么多人工,毕竟卖得也比较便宜。他们的想法可能是尽量减少支出。
小展导师跟两位长期工说,“耿博士”来了,你们有啥事就听她的,但他们并不听小展的。比如种番茄的时候,因为不打除草剂所以地里会长草,小展希望留下这些草,但是过段时间他们就把草拔了。小展还想种点自己想种的东西,但是他们把柜子锁了,不让小展拿种子。小展想施有机肥,他们就不让,说有机肥有其他用处。类似这样的事情让小展很闹心。
再一个困难是,2030年土地租期就要到了,是否续租还在两可之间,这又为如何规划这块土地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导师会有些想法,两位长期工有自己的想法,小展又有一套想法。各方协商后决定,给小展划拨5亩地,由小展独立决定这一小块地的种植方式,这才有了文章开头小展开心的表达。
不过,即便是边角未被开垦过的5亩荒地,要“做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小展说,她现在负责的5亩地原先是荒地,这几年种了些果树,比如枣树、柿子树、梨树等,不施肥不浇水,所以大部分也没有挂果。这块地土壤也不好,种出来的玉米长得特别小,甚至不结玉米穗。所以她从今年开始种了一些养地的草,比如豆科的植物;另外花了一千多块钱完善了水利设施,给地里铺上了水管,这样浇水就省事多了,也更节约水资源。
小展说:“我现在心里其实很着急,明年就是我来的第三年了,一直没有产出不像回事儿。像别人那样养地养个十几年,(这个投入)我可以么?我现在也种绿肥,也施有机肥,我希望这块地快快好起来,明年可以种一些东西,但我不会选对养分需求比较高的作物,而是会选一些抗旱、适应性强的作物。这5亩地只是我的小小试验田,以后是要扩大的,我需要找一些合适的作物,也要寻求一些市场空间。”
“人力就是我一个人,人工成本很低,但我希望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今年最忙的时候就是今年干旱,解决水的问题是头等大事。后面绿肥都长起来了,就定期浇水。对于农场的产品,我会观察农场里常见的野草,思考为什么是这些草能长出来,是氮含量高,还是土壤缺钙?然后就是开发它们的价值。有些所谓的草,在我们这里是草,但别的国家或者是乡野间,可能就是宝,这是让我兴奋的点。一些草我会让它长着,留好种子,以后把野草开发成产品。此外田间的工作没有那么忙,我主要的精力就是做生态农业科普,积累以后的客户群。
我现在也在探索一些消失的品种。我会买一些或者向其他农友要一些老品种的作物,比如玉米、黄豆,或者其他品种,我会把那些长得比较好的,颗粒比较饱满的种子留下来,下一年继续种。第一年长得不好的,我可能第二年也还会再种,看看土壤环境改变了之后,能不能有一些好转。明年我会试着种一点食用香草,除了西餐里的迷迭香一类,我们传统中会用到比如芹菜、芫荽等等,这些作物都种一点,因为这些既可以卖鲜品,卖不掉也可以做干品。这个做到有机的话,我觉得会有市场。”

铺设喷灌后,小展特意养出来的草
三、“散养就生态了么?”——生态农业门道多
现在土地的产出是导师主导,由两位长期工在卖,主要是小麦和油菜,但是很难卖出去;而且虽说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却也都按普通价格卖了,所以收益不高。小展也很希望自己的探索为农场的销售带来一些积极改变。
小展说,她现在有两个较为成熟的单品,一个是小麦(面粉),一个是鸡蛋。虽说是较为“成熟”的单品,也多是卖给朋友、熟人等等,没有更广阔的市场,规模产量也不够。面粉的量,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15亩的麦子,因为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亩产500-600斤。一些大型农场规模可能达到300亩,相比之下,15亩就太小了。现在市场上有机面粉到处都是,哪里都能种小麦,生态农人种小麦的也特别多。普通面粉两块钱,有机面粉可能涨到10-15块一斤。
如何定位,怎样找到市场卖出去,是摆在小展和她导师面前的一道难题。陕西杨凌做农业的公司很多,附近还有两所高校,消费群体主要是高校老师,但是农业学校的福利,经常就是各种面粉。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做面食,有的年轻教师,直接就把面粉寄回家。小展也想过做一些饼干、面包、馒头、挂面,这样价值就上去了。但她的面粉定位点在哪里,创新点在哪里?是否要规划创办面粉加工厂?小展一直在苦苦思索。
小展一边琢磨着产品定位,一边根据自己做生态农业的经验做视频科普。小展做科普的想法主要是从鸡蛋开始的,鸡蛋里面的食品安全也有很多门道,她以前只是简单了解到蛋鸡的抗生素问题,后来才发现还有很多层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有的消费者认为小展的鸡蛋不是土鸡蛋,只有散养的鸡、花色的鸡产下的蛋才是土鸡蛋。小展之前也试过散养,可是鸡都被野外动物吃了,她只得给鸡一个比较大的空地圈养起来,虽然是圈养,但40只鸡的活动空间很大。像这样被圈养起来的鸡在消费者看来就不是土鸡,它们下的蛋就不是土鸡蛋。消费者似乎更多关注的是鸡是否散养,对鸡吃的是什么却不那么关心。如果鸡60-80%吃主粮,剩下10-30%吃虫子,10%吃野菜,这种算不算是土鸡呢?这样的鸡下的蛋就不是土鸡蛋了吗?
其实食物的问题很重要,因为一只鸡,从它吃的每一口食物,到进入人类食物链的鸡蛋和鸡肉,都会影响到鸡和人的健康。但被广泛宣传的,或者是进入大众视线的,只是林下养殖!因为监控好鸡的食物很难,成本也很高,但是制造林下养殖环境,或者是使用土鸡品种但仍延续工厂化养殖模式,容易操作,成本也低。所以大部分养殖者不会去管鸡吃的食物是否健康,但小展很注重这个方面。
因为考虑到要避免玉米里的农药残留等问题,小展不会给鸡喂食外购玉米。但大部分养殖者的鸡都吃玉米,因为玉米能使鸡增肥,而且相对容易采购。这种表面上散养但实际上吃玉米的鸡跟那些吃虫子、吃草的鸡肯定是不一样的。可是大部分消费者是不看这些情况的,那些坚持认为散养的鸡才算土鸡的消费者就不会买小展的鸡蛋。
类似的,面粉类产品,单单拿面包来说,里面就有很多细节需要理解。小麦本身的农药残留问题、磨粉工艺、各种各样的添加剂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以前她只是觉得外面卖的面包可能不健康,但是真正去细究里面的问题,其实有很多需要深挖。她曾经买过一种有机饼干,外包装的配料表只标注了24%的成份,另外76%没有标注,但卖家却告诉她这是商业机密,不需要把配料表里的所有成份都写出来。【编者注:关于食品添加剂,可查阅“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小展说,生态农业产品的认证门槛也是一个很难回应的难题。现在的有机认证是单品认证,而她所在的农场50亩地种的东西比较杂,没有一个突出的单品,就不好申请。反而那种20-30亩都种樱桃或者其他的单品的农场更容易申请有机认证。另外,有机认证能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吗?比如空气干不干净,水干不干净……这个标准也检测不出生物制剂,这里面真真假假的情况很复杂。再就是有机认证每年还有各种认证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这些情况促使小展下定决心一定要做科普,她觉得这也是为未来做积累。不仅是客户群的积累,也是她个人知识储备的积累。生态农业的科普视频相对空白,她虽然更新不快,没有那么强的视频技术,但是慢慢做,总能积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