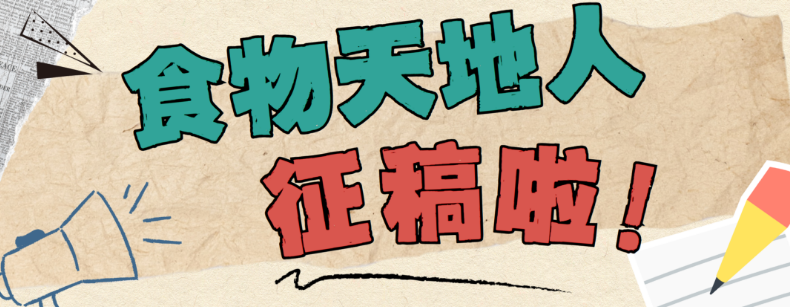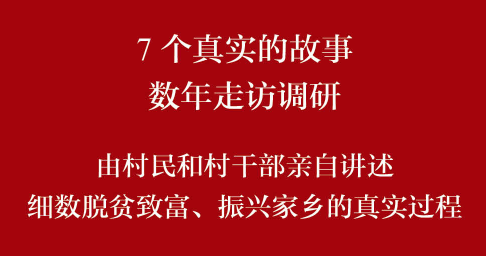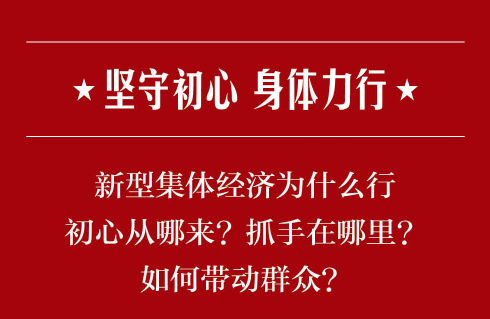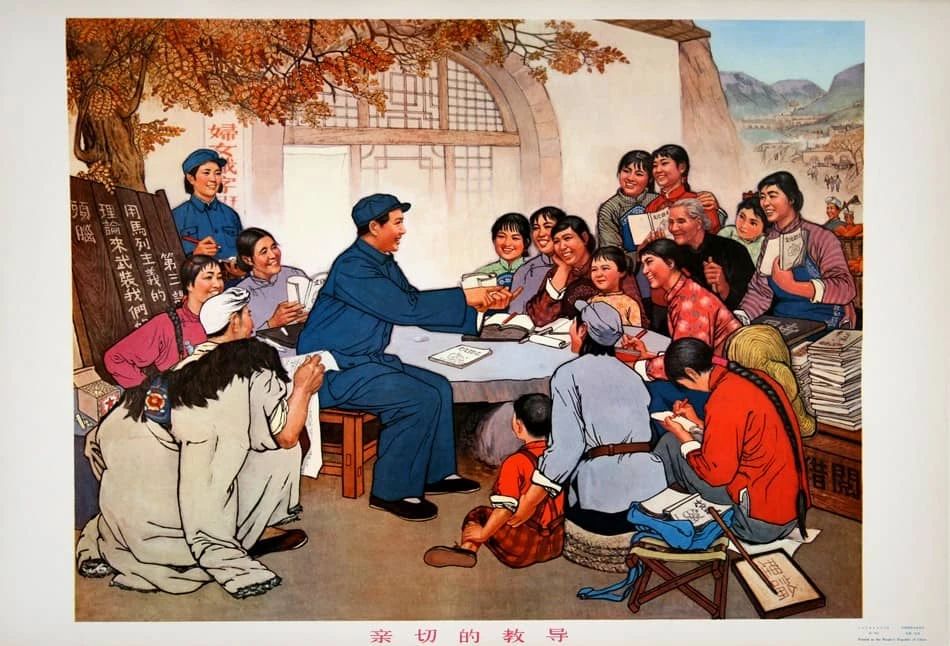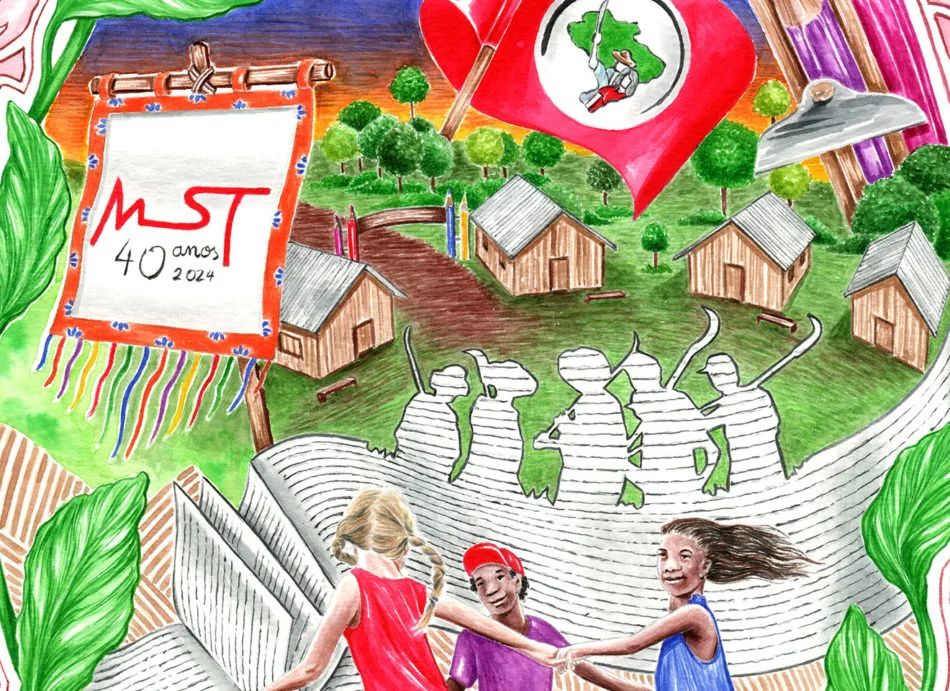读者来稿 | 给村里的河道清淤,只能等待“上面”批项目吗?
来源: 原创 发布时间:2025-09-22 阅读:468 次
暑期强降雨的猛烈雨声仿佛还回响在耳畔,9月已经带着秋的凉意翻开了新的篇章。汛期已过,积水退去,河道里的水也从一个月前的波涛汹涌转为了涓涓细流。C村的村两委班子今天开了一场会,乡里的包村干部琼姐也来了。
顾书记说起被大水冲坏的田间道路:“八月十五就要收棒子了,趁现在没大雨了,要抓紧修”。但是村里资金紧张,让各队干部都盯着机器“快点干”(能一小时干完的别干半天)、“没让干的别干”(能让三轮车过去就不用再弄多么平整了)。又说到这几个月在持续推进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于是会议的焦点来到了村里的河道上。
前段时间的大雨把山上的沙石都冲了下来,“河道几乎要平了,再下雨就淹到路上了”,一名村委相当着急。书记让琼姐看看怎么申请河道清淤和修田间道路的项目,琼姐也挺无奈:“那就是找分管农业的彭乡长呗,但是你得多和他说说,他事情多起来就忘了”。据说,去年县里农业农村局和第三方也来看过河道,但是看完又没消息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看着边上的河道,琼姐抱怨道:“要是说河道清理出来的沙石能卖,给集体增加收入,村里都直接干了,就是怕村干部私吞国家的自然资源。但你说那第三方难道就不自个儿卖了?”之前乡里的晨会上,姚乡长在谈到治理河道的问题时也有强调说一定要确保手续合规,禁止河沙外运,避免百姓质疑。国土资源的红线,深深地画在基层治理的思路上。
这几番讨论对话,引起了我很多思考。首先就是,修理田间道路、清理河道这样几乎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事情,为什么也需要申请上面的项目?背后最直接的原因大概是,没钱就请不来劳动力,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有项目才有钱,才有一切的可能性。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借助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体系,上级政府通过把握项目资金分配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对下级政府的控制权[1]。然而,不仅这一控制模式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其“有钱才能办事”的假设也并非天然成立的社会法则。
这一模式表面上是对人民公社解体后基层政权建设弱化的纠正,但二者根本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项目管理是以物质激励为导向的管理模式,而不是通过抓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人心的大寨精神。这样的“控制”,实际效果如何呢?在C村村委会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若资金来自外界,地方使用资金时的目标便不能仅仅是单纯的“为人民服务”,而是同时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资金,也就导致了田间道路修复要求中的“没让干的别干”。但若是从社区的角度考虑,如果能把道修得更好,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呢?一个以“及格”为标准修出的道路,不仅通行体验有限,而且对下一次强降雨的抵御能力也必将是更加欠缺的。
这里可以看到某种经济理性同社区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导向的管理所造成的结果是对上负责、对项目负责,而不是对群众负责。试想,如果能像大寨那样,充分发动农民的力量去合作进行家园的灾后重建,在人人争当标兵的氛围里,别说是村干部的要求,就算是农民自己,想必也不会仅仅以“及格就行”为目标来开展工作。在集体化时期,像修理田间道路这样的公共工程是村集体统一协调安排,每家每户都会出劳力参加。不仅节省村庄开支,而且促进集体的思想建设:大家是作为村庄的一份子在劳动建设,而不是作为集体的雇员在上班打工,又何来“有钱才能办事”这一说呢?
但是,在河道清淤这个事情上,项目的存在还有更加复杂的用意:请利益无涉的第三方来处置国有资源。我认为,这一安排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不信任。层层审批、外包第三方,说到底是要把地方的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防止地方“越轨”。技术理性的彰显背后,是一种消极监管而非上下同心的合力作为。然而,这样的科层化管理,真的能比交由村集体自主治理更具有利益独立性,从而更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吗?正如包村干部所质疑的那样,看似独立、公正、合乎理性的项目管理,其实很可能满是问题。
且不论等项目、申项目这一系列过程中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耽搁,即便是真正申请来了第三方,他们又将会采用前述的经济理性去开展工程,而非全心全意地去满足群众的需求。毕竟,程序所能保障的仅仅是组织上的形式独立性,而非业务的实质独立性[2]。即便尽可能确保了所聘请的第三方同本地社区、政府无利益牵连,然而在现实的项目进程中,第三方也是由有着真实利益诉求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很难确保毫无私心。并且,相比于村集体,其利益诉求必然是指向其自身而非当地的发展。这进一步导致,村集体需要对好不容易请来的这尊大佛进行监督,以确保资金效用的最大化,而这事实上是在项目的经济成本之上另加了一层组织成本。
由此我们看到一种“信任-效率”问题的吊诡:从实质上说,最有动力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因为得不到上级政府的信任,关键治理权力被上收,转而又被纳入一套符合形式理性的框架中,接受自上而下的控制。而由此带来的恰恰不是理想状况下串联上下级的制度机器之高效运转,而是因其脱离地方现实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解决效率之低下,和各类成本叠加而成的基层负担。
类似的情况并不局限于项目管理之中。以群众监督为出发点的“四议两公开”,初衷虽好,但在“干部动群众不动”的现实情况下,便极易流于一种地方政府和村干部不得不“合谋制造”的秩序表象;为减轻基层负担而开展的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工作,部署安排极为严谨,但流程越多,往往意味着乡镇干部对照上级要求反复修改、制造过程材料(如工作日志)的工作量就越大。这些有着良善用意的制度设计,最终不仅未必能实现其制度目标,反而还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形式主义工作——通过大量的行政文件来自证合乎程序。没有“组织起来”的村集体作为基础,没有以思想政治为挂帅的组织管理,基层政府的治理成本几乎不可能降下来,而再好的制度都会在落地执行中被架空。张怀英在回忆大寨的劳动管理时总结得好:不把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执行的基础上,光靠制度卡人,只能事与愿违[3]。
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中,基层干部只被当作接受规则的客体,而非当家作主的主体。农村自组织的能力和集体的意识愈是被弃置,便愈是退化、淡化,因此其所再生产出来的,也只会是“不信任”的循环。从“村财乡管”到当前广受批评但无从根治的“村章乡管”便是这一体制必然导向的结果。自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解体后,随着政治同社会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开,二者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乃至不可调和。而科层化的行政体制充其量只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协同,而并未实现真正的整合。
此时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给村里的河道清淤,只能等待“上面”批项目吗?我想,不论是从常识推断,还是从历史经验分析,答案都必然是否定的——重建家园并不是某种需要论证申请的项目,而是共同体中每一份子最真切的诉求。然而,这样的能动性如何调动起来,转化为集体的行动力,不仅在村社内部得到支持,而且在制度层面得到认可,仍然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实践推动。
(文中人名均经过匿名化处理)
作者&责编|曳葭
后台排版|童话
参考文献
[1] 渠敬东, 周飞舟, 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6): 104–127, 207.
[2] Michael Power. 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 张怀英. 村民干活不积极怎么办?学学大寨的劳动管理[EB/OL]. [2025-09-03]. https://shiwuzq.org/article.html?aid=1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