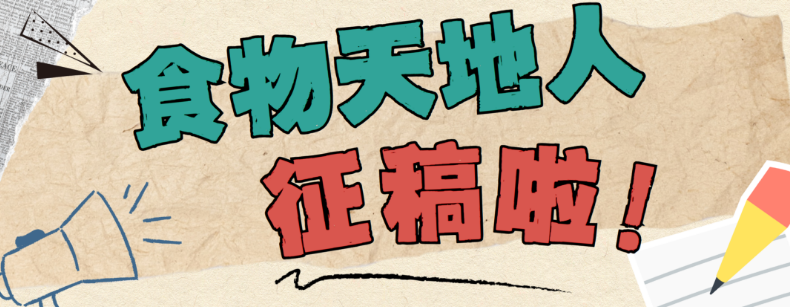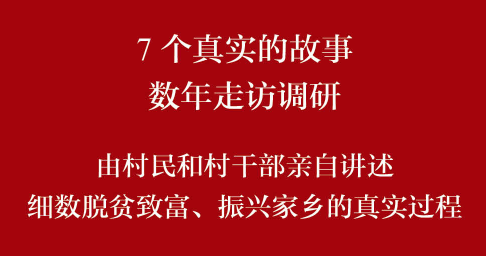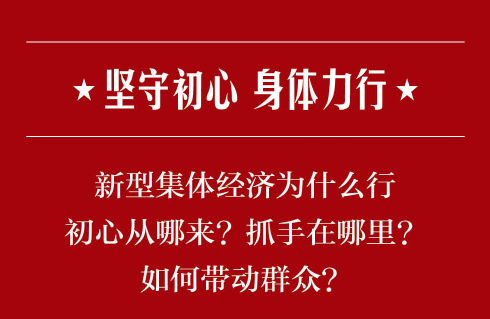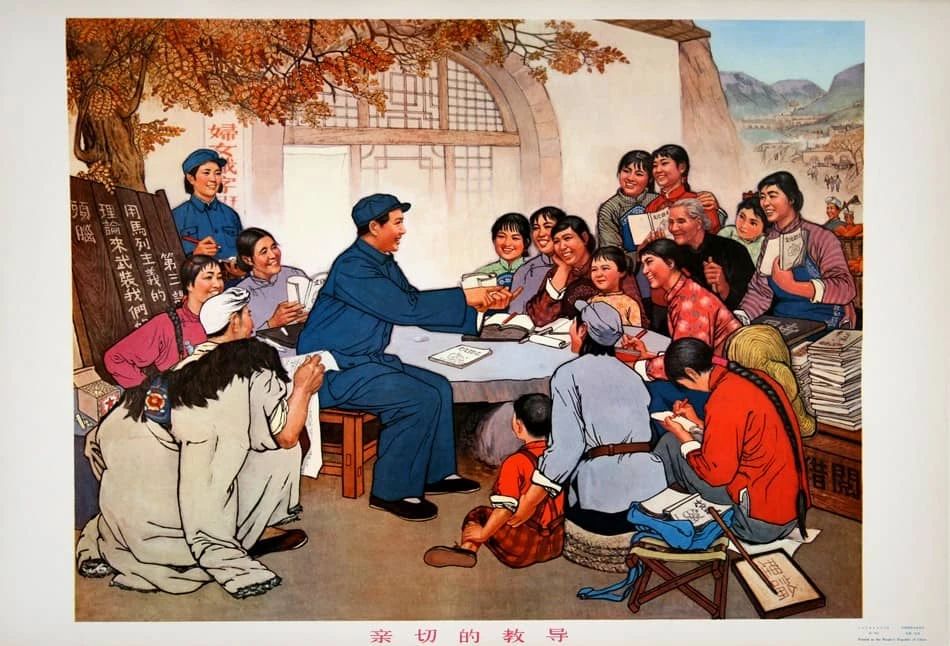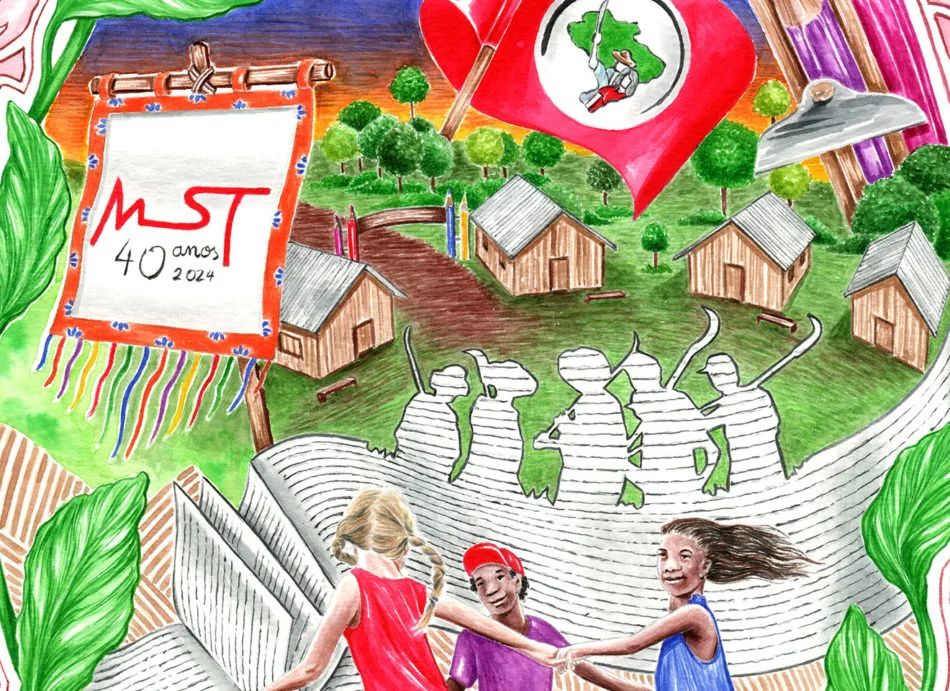“胜利”的背后:谁盗走了印度农民运动的果实?
来源: Socialist Project,部分内容源自笔者在《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上的文章。 发布时间:2025-11-14 阅读:678 次
导 语
关注国际农政议题的朋友或许还曾记得发生在2020年的一件农民运动的大事件,当时莫迪政府强势推动三项明显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农业立法,一场席卷印度、持续一年之久的农民抗议运动也旋即爆发。它不仅是现代印度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农民斗争之一,最终还成功迫使政府收回成命。然而,当胜利的欢呼散去,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也浮现出来:这场看似大获全胜的运动,最后却被其他保守的社会力量“摘桃子”,原本应成为核心的阶级政治议题反而遭到边缘化。
那么,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印度农民,尤其是最贫困的农业劳工和无地者的命运?为何一场初衷美好的斗争,最后似乎悄然变了味道?本文将带领读者重返当时运动的中心——旁遮普邦。在这里,作者帕拉姆吉特·辛格将眼光瞄准在左翼团体内部,在他看来,领导农民运动的左翼农民工会联盟内部还存在着斗争路线的分歧以及政治斗争中的诸多不成熟之处。对于关心社会运动、农业问题与全球南方抗争的读者而言,这篇针对农民运动的反思,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宝贵的参考视角。
作者|帕拉姆吉特·辛格(Paramjit Singh),是一位专注农政研究、政治社会学和全球南方研究的学者。他目前任职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以及印度昌迪加尔的旁遮普大学。
译者 | 缇戈、psq、侯憨、鹅童
校对 | Alvin
责编|侯憨
统筹 | 卓嘎
后台排版|童话
在当代,全球南方依然保存着数量可观的农民群体,而帝国主义又亟需将这股社会力量收编整合进入其资本积累的网络之中,这两者共同催生了一个新的农政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帝国主义国家借助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制定和策划各类政策与行动,来向南方国家施压,从而推动农民群体整合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近年来,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新动向,即南方国家中的右翼势力日益得到大型企业资本的鼎力支持。
印度作为一个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农民群体,全国约55%的劳动人口,其生计直接依赖于农业。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印度政府就相继推出三部农业法案(《农产品贸易与商业(促进和便利化)法案》《农民[1]价格保障和农业服务协议(赋权与保护)法案》以及《基本商品(修正)法案》),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铺垫,它标志着印度政府将本国农民完全纳入大型农业资本的直接统治。此举在印度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运动历时一年之久并最终迫使政府废除了这三项法案。
农民运动的影响极为直观地反映在了近期地印度大选之中,作为推动农业立法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迎来“现世报”,它们在农村地区的议席遭遇断崖式下跌。这场抗议运动在印度农村地区也催生了新的社会意识,削弱了印度人民党的教派政治。在2024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在398个农村选区中仅赢得165席,席位较2019年的236席已经大幅缩水。
印度人民党之所以遭此重挫,不仅是因为该党执政期间以威权手段将农业与大型企业资本进行强行捆绑而触犯众怒,也是因为该党始终未能回应和满足农村地区的核心需求,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就业机会创造等。
一、对抗莫迪政府的农民工会
旁遮普邦是2020至2021年农民运动的策源地。彼时,当地的农民工会就率先发起了反对农业法案的动员,随后抗议的浪潮又迅速席卷至哈里亚纳邦、北方邦以及拉贾斯坦邦的广大农村地区,而旁遮普邦的左翼农民工会则始终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线。
单从土地面积看,旁遮普邦仅占印度国土面积的1.5%,但这片土地又是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是印度国内规模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旁遮普邦的土地是如此富饶,以致历代的印度统治力量(从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官商勾结势力)无不密切地瞄准这一块“唐僧肉”。在这种背景下,旁遮普的农民群众,作为全印度组织程度最高的农民群体,为了守护自己的土地,与这些强大势力进行了一次次斗争,谱写了悠久的抗争史。
比如,早在1907年,旁遮普农民就曾因英帝国主义的政策侵害其土地权益和破坏农业生产,而展开了长达七个月的艰苦斗争。百余年后,又是旁遮普的农民领导了2020-2021年的抗争,这场运动无疑已是现代印度历史上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农民斗争之一。这场农民运动的意义在于其广泛的动员、有效的抗议策略以及强大的包容性。
诚然,过去的斗争有上述优点并且促成了废除三部农法的直接胜利,但这场运动却未能更进一步,推出一项社会主义的纲领。在旁遮普,锡克分离主义势力钻了空子,他们反过来利用运动来推进他们自身的政治诉求,扩充自身的影响力。
二、印度人民党的亲企业议程与农业民粹主义力量
数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印度的政治经济,自2014年大选后,印度人民党又获得了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空前支持,国内外资本对右翼政党的这种力挺撑腰,使得新自由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民党政府完全顺应了帝国主义与本土资本的要求,它们掌控着印度的政治经济,极大地加速了印度国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
在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约9亿)生活于农村,但大型企业资本对农村经济的渗透和整合又是极为有限的,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主要以农业、小生产以及各类农业与非农务工为生。在国内外资本的重金资助下,人民党政府则费尽心机推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议程,力求将印度农村并入大型企业资本的体系中去。
在疫情肆虐之际,民众本期盼着政府能够出台财政刺激措施以缓解民生困顿,人民党政府却选择在此时逆势强推三部农业法案,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倒行逆施,它旨在加速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执政的人民党仗着多数议会席位的优势,笃定农民群体不会形成多少有效的抵抗,更何况印度的国家机器在此之前就曾动用过强力镇压国内的少数群体运动,他们对此有恃无恐。除此之外,人民党推动农法还另有盘算:他们以一种威权独裁的方式力推立法,既未经民主审议,也未与各邦政府协商,这无疑是对印度联邦制度的一次公然挑战。
三部农法的废除标志着农民运动的胜利,也揭示了人民党政府对农民群体力量的严重误判。回顾2020-2021年,彼时农民抗议刚刚兴起,印度各大全国性的正式工会组织几乎都畏缩不前,它们不敢挑战右翼威权政府的反人民政策。与此相反,各地的农民工会以及心系公众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他们积极地向民众阐释农业立法将对收入、土地权利以及种植自由造成何种负面影响,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得运动得以开展和延续。同时,农民们不愿丧失政府所保障的最低收购价,害怕失掉自主种植权,这些经济诉求和现实利益也是广大农民之所以能够在工会中实现动员组织的关键性因素。
这是21世纪以来,印度农民首次以如此庞大的规模站出来,在全国范围内挑战帝国主义的政策议程。这场运动由旁遮普邦32个农民工会组成的统一战线——桑约克特·基桑·莫尔查(Samyukt Kisan Morcha, SKM)领导,运动随后又获得了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一个囊括近400个农民组织的平台)的支援。除此之外,来自其他各邦的工会,国内外心系民众的进步组织,乃至海外旁遮普侨民也纷纷加入到抗议的行列之中。
在这场斗争中,农民工会的领导层采取了别具一格的抗议策略。抗议者们和平地封锁了通往印度首都德里的主要道路,对首都的经济循环构成重大打击。这一策略最初是由旁遮普邦印度农民联盟中的团结-乌迦罕派(BKU Ekta-Ugrahan)推广开来的[2],他们最初就是用这种抗议方式来针对当地的大型企业实体(如信实集团的加油站、购物中心、阿达尼集团的粮仓和收费站)。
除此此外,地方歌手、妇女、学生、运动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共同构成了本次运动的一大重要特征。学者们尤其强调运动中形成的这种跨阶级与跨种姓联盟,在他们看来,要挑战印度的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图谋,建立这种跨越阶级与种姓界限的联盟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一个跨阶级跨种姓的联盟是何以造成的呢?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不断加深对农业部门的统治,企业与金融寡头的利益得到优先满足,而这也威胁着农村既存统治性阶级(比如富农)的利益和地位。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渐式微,乡村精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下滑,小农、农业雇工与非正式工陷于日益严峻的贫困处境,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跨阶级与种姓的联合。
相比于以往的农民运动,妇女的积极参与也是这场运动的一大突出特点。起来斗争的妇女有相当数量来自于旁遮普邦的小农家庭,边缘农户家庭甚至是无地的达利特家庭(注:达利特为印度传统种姓制度中的最底层群体),在运动期间,她们就长期扎营在德里边境。妇女之所以会如此积极地投身运动,有部分成绩要归功于团结-乌迦罕派的组织工作,它们早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就成功动员了超过五万名女性工人和农民参与斗争。
运动的胜利让过往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人们联想起印度农民对抗英帝国主义苛政暴行的漫长抗争史,回忆起农民在当时也曾与进步力量联合抗争并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大部分学者认为,2020–2021年农民运动的胜利充分证明,和平而持续的抗争能够有效遏制帝国主义与威权联盟的反民主倾向,仍然具有显著效力,这对未来的进步政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过,也有少数对运动的成果提出了不同评价,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认为,从农村贫困人口的立场看,农业民粹势力最终纂夺把持了运动,阶级政治的议题被边缘化,应对农业问题的平等主义方案和举措也因此受到搁置。
三、农业民粹主义还是阶级政治?
须知全球性的帝国主义与印度国内的国家-企业联合体已经达成了联盟关系,而当我们回顾2020-2021年农民运动的诸多叙述时,就会发现大部分叙事尽管内容详尽信息丰富,却并未采用阶级视角来理解这种结盟关系的复杂性,也未能洞察农民阶级内部的动态关系。现有的叙述方式不仅不利于我们认清农民的真实境况及其斗争态势,也掩盖了农民内部不同阶级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现实。
我认为,要想充分理解帝国主义的农业整合计划,并准确把握与之对抗的农民运动,就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要求我们既要审视帝国主义从外部对农业农村的侵蚀,又要关注在此进程中,地方政府所充当的角色以及农村特权阶级所发挥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这场运动时,都偏重于描述其斗争特点与成功之处(这在当时或许是必要的)。然而,他们的分析方法往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热衷于呈现易于理解的叙事,却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角进行透彻审视。令人惊讶的是,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是结合日益严峻的农业危机与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侵蚀这一宏观背景,来理解和认识2020-2021年农民运动的。我认为,这种脉络化情境化的分析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揭示农民运动背后的深层权力博弈机制及其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意涵。
由此,我们得以对印度旁遮普的农民运动提出一项批判。历史分析表明,自七十年代绿色革命技术在旁遮普推广后,一个新兴的富农阶级便掌控了当地农村的农业生产与政治。自那时起,该地区的农民运动往往趋于保守,旨在维持现状,而非推动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参与2020-2021年斗争的多数民粹主义农民工会,其领导层正是这些富裕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因此,一旦触及真正关乎农村边缘阶级的社会问题与经济贫困议题时,这些工会实质上还是依附于资本主义阵营一边。如果我们仔细回顾整场农民运动的运动目标演变,就会十分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农民运动最初提出了八项要求,这些要求原本就包含了对边缘群体诉求的回应,尤其是对无地劳工、贫农和佃农需求的回应,但随后运动的目标出现了退化,并最终演变为只寻求废除三部农法。
为了厘清领导权问题,我将那些直接或间接受毛派思想影响的左翼农民工会划分为两大类。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虽然旁遮普邦还存在着其他左翼工会,但我目前的分类只考虑左翼农民工会中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那些团体。在我看来,农民抵抗运动之所以未能彻底地改善农民和农村劳动大众的处境,未能实现进步性的政治变革,其主因就在于:这两类左翼团体在对农民具体物质现实的认识上依然存在分歧,他们各自固守自己信奉的教条,正是这种认识的僵化,衍生出了它们的各自弱点。
这两大左翼团体在纲领上都反对帝国主义,都抵制帝国主义对印度国家机器的渗透和支持,但在具体策略上,他们的行动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别,他们在结盟的策略上就存在特别大的差异。
以印度农民联盟中的革命派(BKU-Krantikari)为首的左翼团体认为,要挑战帝国主义以及与之勾结共谋的印度国家,就必须团结同样反对国家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他们反对将印度视为是一个印度教多数主义的国家)[3],将其纳入政治行动联合之中。该派领袖认为,这些分离主义者能够成为其革命斗争中的“雅各宾式”先锋力量[4]。但是,他们却忽视了锡克分离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意识形态空洞”。
萨米尔·阿明在别处就曾论述过这种空洞,这种空洞的根源在于,锡克教分离主义者虽然在名义上声称自己追求宗教或文化目标,却并不真正关心神学讨论,而只热衷于“通过仪式化的行为来凸显其群体身份”。这种唯宗教论的做法,使他们得以回避了真实的社会矛盾,即边缘化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分离主义的这种空洞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农民运动从反帝、反阶级压迫的性质,蜕变为单纯反印度教多数主义国家的运动,这只会将社会带入僵局;
其二,他们斗争方式虽然看似激进,却缺失了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剥削的解放性纲领,这反而为国家的镇压手段提供了合法性,国家可以以“维护统一”的名义来打压真正为边缘群体发声的运动。
在这里,我有必要提醒那些意图联合分离主义势力的左翼工会,他们应当认识到:分离主义势力在社会层面上究其本质是倒退的。在旁遮普的农村地区,他们常常推崇封建制度,固守所谓的“正统”价值观,并热衷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及生活方式。更紧要的是,他们在农业危机最深重的地区并无多少实际的影响力,因此也无法切实地为底层民众反抗体系性的贫困提供多少有意义的支持。
另一个毛派团体(以印度农民联盟中的团结-乌迦罕派以及基尔蒂农民工会为代表)则认为,大众的觉悟与日常的抵抗才是动摇资本-帝国主义的正道。他们不主张与文化主义者以及宗教势力的结盟。他们反而批判这些群体,指控他们扰乱了人民反资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前文谈及的革命派团体也经常回敬他们以批判,认为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议程。革命派的这种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后者信奉日常抵抗,却没有将这些斗争与前瞻性的具体政治变革结合起来。他们热衷于号召人们抵制选举,但抵制选举又如何能减轻贫农与农业劳工的苦难呢?对于这一点,他们就缄口不言了。
我认为,第二类毛派团体的抵制策略在今天已经了一个恶性循环:即只知道反对掌权的政府,却无法提供一个可行有效的替代方案。他们并未认真地对待工会成员的阶级意识培育问题,没有严肃地去探索一条铸造政治主体性以抗击现存权力结构的路径。讽刺的是,他们一方面空谈“群众路线”的思想,另一方面却不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建立自身的政治主体性(即政党),而幻想可以在这种条件之下就匆忙地去夺取国家权力。在我看来,何以解决这个矛盾,是我们今天要实现进步性政治变革所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四、重拾阶级政治:左翼团结的再出发
总而言之,左翼工会虽然为运动付出了努力,但这种努力也为锡克分离势力和民粹主义农民工会的活动打开了空间,2020-2021年农民运动的走向最后也发生了转变。其结果是,运动从一股进步的政治力量蜕变为维护现状的保守力量。锡克分离主义者利用农民工会的平台,腐蚀绝望青年的思想,将其用作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工具,从而壮大了自身议程。他们在2024年大选中从旁遮普邦赢得了两个人民院席位。这一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左翼工会未能将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在大选期间缺乏对支持者的有效引导,致使他们不知该为何投票给左翼政党。
我认为,为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进步的政治变革,左翼工会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战略思路,重新考虑意识形态同盟,并批判性地评估自身在2020-2021年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在此背景下,我在前文分析中提出的两个关键结论亟待认真探讨:首先,研究旁遮普乃至研究全球南方农业问题、帝国主义与农民抗争的学者,不仅要关注帝国主义利益实现与农民权益维护的矛盾,更应该深入审视农民运动的内部动态博弈。这一审视对于我们理解贫农与农业劳工所面临的特殊困难是极其重要的。对左翼团体来说,一个核心的问题应当是:究竟需要何种政治策略,才能打破现状而推动进步的政治变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仅仅是毛派或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的洞见能够提供宝贵的指引。
其次,左翼组织必须在内部实现团结,并与左翼工人工会联合起来,用一个旨在实现进步变革的政治纲领去挑战资本-帝国主义体系,而不是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去汲取革命动力。
译者注:[1]笔者清楚“农户”(farmer)与“农民/农民阶级”(peasant)的差别。一般来说,“农户(farmer)”强调职业性质而非阶级属性;“农民(peasant)”则带有阶级意味。在部分语境下,peasant也可译为“小农”。但在中文语境中,“小农”与“农民”在阶级属性和生产规模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为保持语义一致,减少混淆并使得文章便于阅读,本文统一使用“农民”一词。
[2]这里需要指出,BKU(Bharatiya Kisan Union),即印度农民联盟,并非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某一个农民工会(union),而是一个农民工会联盟,印度农民联盟在印度农民运动历史中长期存在,规模庞大但内部派系林立,不同的派别由不同的领导人带领,信奉不同的斗争策略,而BKU Ekta-Ugrahan指的是在印度农民联盟中的一个具体派别。
[3]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复杂的教派对立和矛盾,所谓“印度教多数主义”,指的是将印度国家重塑为一个以印度教文化、价值观和多数群体身份为核心的国家,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种民族(即印度教民族)。而锡克教分离主义则认为当前的印度国家政权偏袒印度教多数群体,压制少数群体,代表的是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的利益和意志,因此他们追求独立建国,谋求政治和文化自决,反对由一个以印度教为中心的中央政府来统治他们。
[4]所谓“雅各宾式”先锋力量是一种政治隐喻,它一般指的是一个激进的具有严密地下或半地下组织能力的,并且能够将革命推向极致顶点的先锋力量,但如读者所见,作者在这里又特意给雅各宾式四个字加上了引号,这代表作者对这个判断持一种批判态度。
文章来源:Socialist Project,部分内容源自笔者在《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上的文章。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project.ca/2024/08/peasants-and-politics-neoliberal-india/
原文标题: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Neoliberal India: The 2020-21 Peasant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