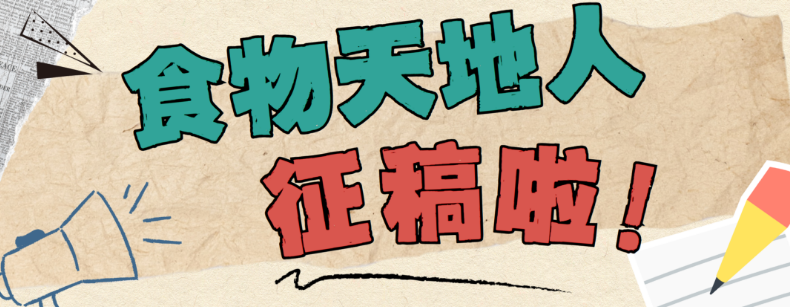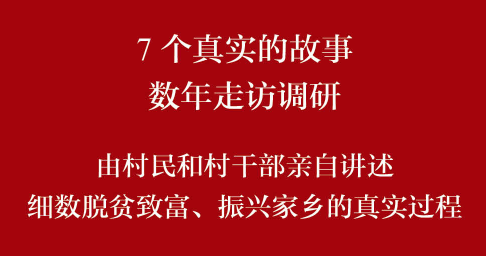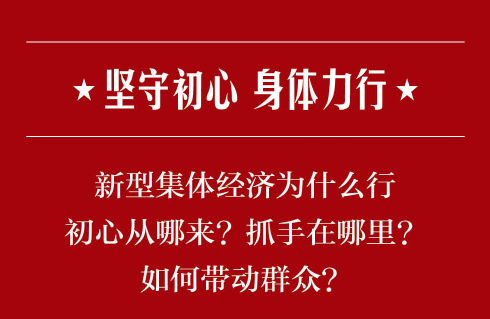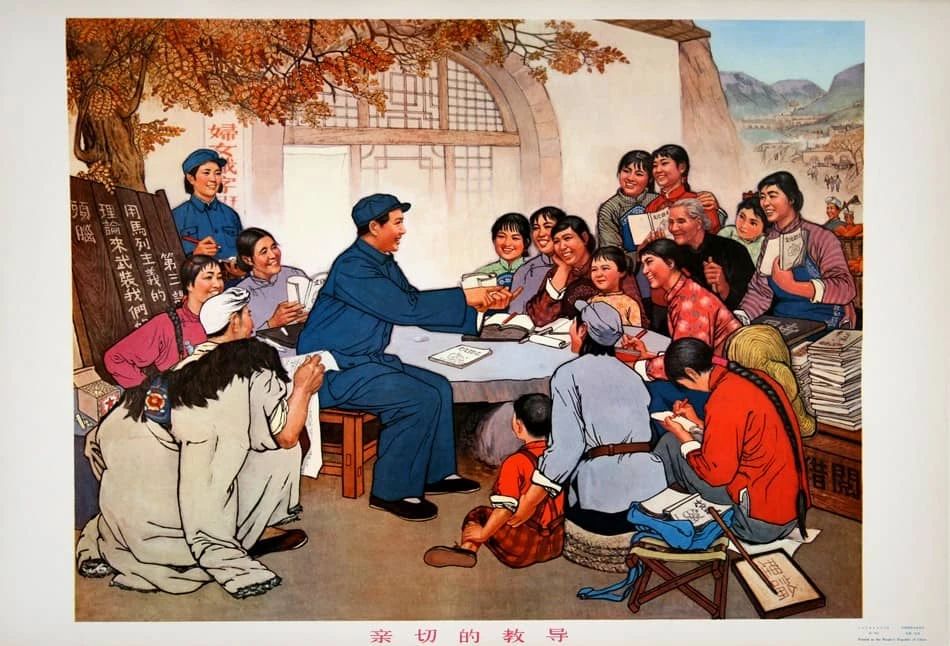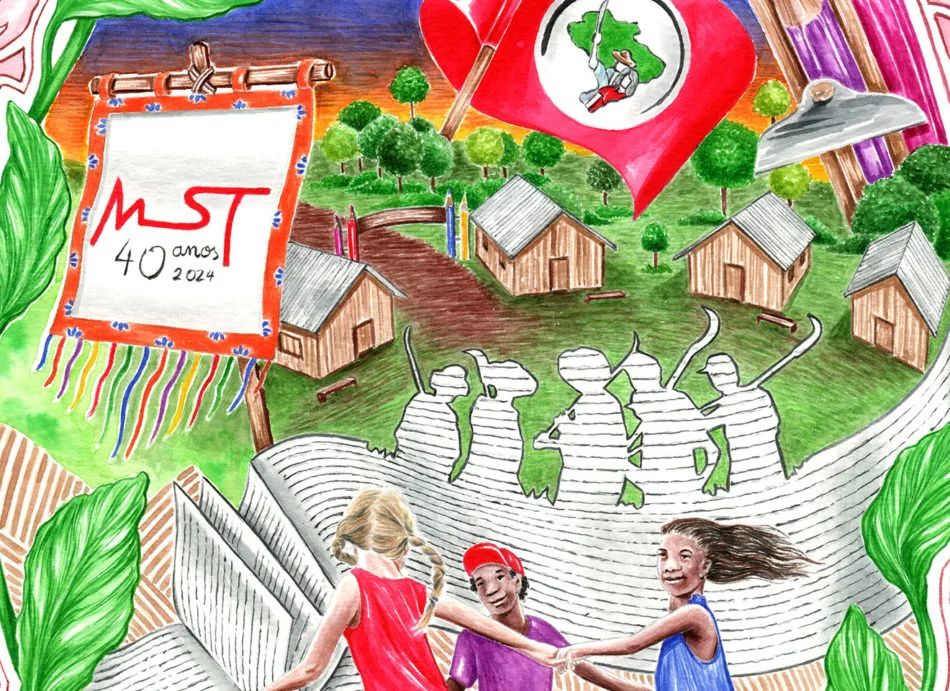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买有机肥或菌种?自制菌种的
如果说,我们不能创新业态,建构一个不同于农食过度商品化市场的新市场机制,那么,充其量,我们就只能是右手赚钱,左手做公益的罗宾翰经济模式(当然这也很是重要的一部份)。
星期二, 十二月 25, 2012
关心好食机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其中工作就是在部落的果园,和农友们一起利用附近原始森林的土壤,培养自制的菌种,然后运用这些菌种改良土壤并制作各种堆肥。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跟朋友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友善环境当然是其中一项目的,但是,如果只是要友善环境,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买有机肥?如果是因为有机肥太贵,要自己堆肥,为什么不直接到市面上买菌种回来就好?菌种并不贵,不是吗?
必须从表面的问题看到深层的结构,否则,行动就会事倍功半。因此,我们坚持这么做,不单纯只是因为友善环境以及经济效益的考虑(其实严格说,要看以什么尺度计算经济效益)。今日农民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事实上与现代农业高度商品化的过程是环环相扣的,并且,背后还有现代科学和技术的「不当」介入的推波助澜。
让我从一个故事讲起这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几个月前,小君第一次到教部落跟年轻一辈的原住民果农「示范」怎么自制菌种,带他们到同流域的原始森林采菌回来家里繁殖培养菌种时,突然,路过的Yagi(长辈女性的称呼)停下来跟我们说:「我们以前也有这样……」,她说,以前的他们会收集家里的剩饭,拿到森林放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等剩饭发霉后,再拿回果园(或田里,以前双崎部落有种水稻),施做到土壤里面。
Yagi的话让我脑袋动了一圈。我想的倒不是他们有类似的技能和「知识」,而是,这些怎么都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又,在消失的同时,他们改变以依赖化肥、农药种植?这个改变提升农作的「效率」吗?这个转变的过程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外界的力量在这个转变的过程,起了什么作用?社会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图:左边那位Yagi是部落与我们一起合作农民的母亲,她看见我们自制菌种时,跟我们分享起过去老一代族人把剩饭拿去森林里置放的传统方法。)
去技能化的农民同时失去了市场上的对抗性
显然,现在的农民大部分都依赖「资材行」耕种。土壤缺肥怎么办?来,问资材行老板要加什么肥料。农作物生病怎么办?来,再问资材行老板用什么药。平常没事想获取农业新知怎么办?来,也是到资材行问问老板,最近有没有发明新药或肥料,让农作物可以长的头好壮壮的?正如部落的农民有一次开玩笑跟我说:「现在管理果园很简单,连砍草都不用了。谁都嘛可以种!有问题去找资材行(农药行),问他们喷什么药,买回来喷一喷就好了。」
当然,资材行有好有坏,我们也遇过好的资材行,不会滥用化肥和药剂(例如东势的「三合一农业社」)。但重点是,现代农民凡事依赖资材行的现象背后,其实有一段农业商品化的过程需要进一步思考。
在欧洲的历史上,农业商品化主要是伴随着企业资本圈地,农民失去了生产工具变成单纯的工人,从而成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台湾,尽管农业生产还是以家庭式农场的小农为多数(非企业农雇工生产的模式),表面上看来,这些农民好像仍保有生产工具,没有完全沦为无产工人,但在台湾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中,这些农民却仍然在日渐成为「专业农民」之时,深困在商品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为了廉价劳动力的贩买者。问题是,商品化的现象并非在农业部门才发生,但为何农民的处境会特别艰困?这其中,我认为,这与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农药、肥料等资材)全面透过商品市场取得,有一定个关连。
回顾历史,早在1930年代开始,台湾便因岛内货币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提高了人民生活对现金的依赖,不仅一般生活所需逐渐依赖透过市场货币交易完成,农务所需的生产资料,也逐渐被迫从市场取得。以肥料为例,1918年米农有56%的肥料是自给的,而到1934年,降到34%;同期的糖农,肥料自给率则从42.8%降到21.4%。到现代,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几乎现在惯行农法的农民,已经接近100%依赖市场农药、化肥作为农务过程的主要生产资料。然而,农民依赖市场取得农作资材,并不是单纯从市场买回他们「本来就会做的东西」,而是买来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东西」。以肥料来说,市场贩卖的肥料,是工厂生产的化学肥料,而不是农民土制的那种堆肥,这样一来产生了两个影响:
1. 农民丧失原先技能,降低原本农作过程所需的个人特殊化技术含量,提高了对资本的需求。过去农民高度依赖自制肥料时,尽管多数情况效率比化肥低(其实并非必然,这个问题稍后讨论),但农作过程中,农民个人的技术含量却是相对高的,个别农民生产的状况的差异性也大。然而,一旦依赖化学肥料后,农民在生产过程的个别技术含量降低、对如何选用化肥知识需求提高了,彼此的差异也降低了。并且,农民不但用钱到市场上买农药、肥料等等资材,并且,只要资本越充足,农业科技就可以赋予农民越高的「逆天行事」能力。比方,肥份不够?没关系,多下几包各式昂贵的高级肥料;想要抢收早市卖个好价钱,来,催熟剂加进去。高度依赖轻易可以从市场上取得的化学制剂,农民的耕种陷入了资本投资的金钱游戏。如果说西方农业的历程是农民被剥夺生产工具以致沦为工人,台湾则是农民被剥夺技能和传统智慧,沦为单纯的劳动力!
2. 农民因技术含量降低,农务过程的劳动价值因而也降低,并且由于化学制剂使得农民可以量产,并且扩大了同类农作物的生产范围,农产商品彼此的竞争变的更为激烈,农民只好透过剥削环境来增产,以追求利润。试想,当生产变容易,许多农民都能种出相同的东西时,农民靠什么竞争?直观的答案就是:产量!产量!产量!而为求产量提高,过度使用肥料、农药的情况便层出不穷。最终,农地活性丧失,生态平衡破坏了,农民需要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到头来,小农赚取的收入连付农药和化肥的资材费都不够,农民、彻澈底底成为最廉价的劳动力。诸如此类的故事,我们经常在小农身上听到,并不陌生。
换言之,农业生产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从自给自足或特定交换关系下以物易物的产品,变成专为在市场上换取货币的农作商品。在台湾,市场便于取得的化肥和农药资材,正是完成这一农业「彻底商品化」的重要机制。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光光改变不用化学肥料和农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设法找回农民在农作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让技术回到他们身上,而不再垄断于专家或资材行身上。
赋予农民主体性的适当科学知识与技术运用
因为思考到这些问题,我们意识到,只是推动友善环境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友善环境仍然是依赖商品市场的机制购买有机资材回来使用,那么,商品市场的机制终究还是会使得农民陷入不可翻身的困境,这样一来,「友善环境农业」绝无法在小农间有效推展,最终只是会养出像郭台铭开设永霖农场那样的有机企业大农。然而,自制堆肥功效、透过生态多样性控制环境的病虫害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会不会还没到终点,我们就先阵亡了?
于是,我们回头思考,到底,这当中出了什么事,真的没办法吗?
这过程中,多亏了小君学过KKF的农法(请连结此处观看:一切从「土壤改革」开始:养益菌一点都不难!),使得我们的想法不至于空谈,有实做的可能,而在实做过程中,我们也慢慢体悟一些事情。例如:自己从果园附近森林土壤采集培养出的细菌,尽管存在一定失败率,也不如市面上单一菌种的功效强大,但是,到底多强大的功效才够强大?重点显然不是多强大的问题,而是我够不够用的问题。够了就好,我何必盲目追求效用?又,难道过去农民自制菌种就一定只能盲目土法炼钢,不能提升效率吗?科学技术只能为资本服务吗?或许一开始知识与技术的使用就走错了路也说不定。
思考到这些问题,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引导部落农民操作的农法,不能直接告诉他们用什么菌、按照什么步骤施用这种「去智化」的SOP,必须带给他们一套实证的方法、科学的知识和反思的态度,才能让他们可以有能力不止是盲目的土法炼钢,又不至于自卑地崇拜科技和无限的追求效率。事实上,我们所运用到的生物知识范围,并不超过高中程度的生物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论,就足够让他们运用周遭环境资源,自行培养菌种,且以更严谨的方式和态度,判断制作成功与否。而且,整个过程,充满了对现代科学技术无度地服务于资本的反思。

(图:或许,现代文明对地方文化可以不必再是掠夺式的窥探。)
比方说,我们不止让农民做,更强调他们必须每个环节的理解道理。为什么到同流域的原始森林采菌?因为同流域土壤类似,而森林里面的土壤较能找到适合该土壤的多样性原生菌种。到了森林后,不是乱采表土,先观察树木的健康状况,判断哪几处表土较好,然后分散几处采集(通常是采集高大树木底下的表土),做上编号后,别上放入不同编号的培养桶,加入适量糖蜜、米糠和水,充分搅拌后,置放一周。其间观察记录不同培养桶分解糖蜜的速度、味道、表面长出的真菌类型,从而区辨哪一桶菌的功效较佳。另方面,我们也砍下一些果园里杂草,分别加入不同培养桶的菌种,观察哪一桶菌最能有效分解杂草,甚至,我们还可以试验培养过程搅动和不搅动,以改变好氧菌和厌氧菌,来找到最合适自己农地的菌种。

(图:透过简单的实验,就能找到最适合分解杂草的菌种了,「科学方法」其实也可以很实用,不必关在实验室。)
这些方法一点都不难。我们进一步让部落农民思考比较,这跟过去部落老人拿剩饭到森林里面放到发霉的做法,目的再让他们了解,我们不过是用「相对科学的方式」,提供更有效率和可检验的过程来繁殖菌种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传达,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距离农民传统地方智慧其实没那么遥远,并且,以在地升级、保留他们主体性的方式运用科学,才是适当的科学和技术态度。
想想,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完全不同于现在农业科技的态度?现代科学并不服务于农民和在地智慧,而是把原本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智慧和技能剥夺走。他们从森林里采集表土,然后到实验室培养菌种,然后分析出一只一只菌之后,命名并申请专利,最后再卖给农民。当然,不可否认,的做法有一定的意义,比方当植物感染病虫害时,确实需要单一菌种来处理,而且,也不是所有研发单一菌种的技术专家都是恶质的商人,像是蔡18菌的发明人,就相当友善农民。但毕竟多半时候,农民并不必依赖这些高端的专业技术,他们只需要最简单的科学态度、生物学常识,就可以自己在他的果园实验、培养多样性的菌种来活化土壤。然而,当主流科学都走上实验室这条路,而不把知识与技术回到农民身上,协助他们在地智慧升级时,最后农民必然因土法炼钢术效率过差而放弃,转移到市场上花钱了事实。

(图:透过适当生物科学知识和实证方法的导引,农民要成功自制菌种并不难。)
同样的方法,我们也用在堆肥技术的在地提升上。一般传统农民自行堆肥,并没有针对氮、磷、钾等不同养分,尝试堆出不同的肥料,因此,效率不会太好。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堆肥一开始,我们先将土壤送到农试所检验成分,再依农试所的报告和建议,了解需要哪一类型的养分,再进一步思考如何就地取材,堆出这些养分。(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这个过程,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前去观看:农民缺钱,土壤缺氮,怎么办?——就来作液肥吧!)
举例来说,我们发现缺乏磷肥。怎么办?如果只是想要友善环境,那很简单,去买有机磷肥或者海鸟磷肥不就罢了?我们认为的适当科学知识和态度不是如此,而是要能设法降低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提高自主性。于是,我们透过查询,知道磷肥来自海草,以及吃海草的生物,那么最简单的办法,不正是到附近市场,搜集鱼贩每天剩下的下角料来堆肥就可以了吗?于是,我们开始搜集起附近市场鱼贩的下角料,没想到,我们还意外的发现,此举解决鱼贩们每日困扰的问题!
光是土法堆鱼的下角料是不够的,因为鱼会发出恶臭,最终农民一定受不了放弃。但,我们不是已经会自制菌种了吗?我们何不透过相同的实验方法,从土壤的多样性维生物中调制最适分解鱼的比例呢?果不其然,我们很快就找到让鱼不会发臭的方法,而且,只要一个多月,一桶40斤的鱼肥就制作完成了。
这是我们在部落做的尝试。我承认,这样的效率当然不及农民直接到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有机肥、有机资材,但重点是,我们有必要追求这样的效率吗?一个月堆肥的时间不能等吗?一个星期自制菌种的时间太漫长吗?相对起失去的主体性,那个严重?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到底什么才叫做效率?

(图:自制一桶40公斤的鱼肥需要一个月,虽然比起直接到市场买「没效率」,但其中丰富的社会意义却是无价!)
农民重拾技能才有主体性,有主体性才有对抗市场的POWER
有人会问我们,难到你们要搞「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吗?我跟小君听到总是苦笑一番。
我并非反对一切商品市场的死老左,更不是万恶资本主义那种不务实的浪漫左派。问题是,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思考,即便资本主义不是万恶,市场经济有其功效,但,是否意谓着我们就应该将全部的社会生活整并到商品化的市场经济里头?是不是有些部分,「性质上」并不适合整并在现有商品市场的经济体系中?比方说教育、农食、媒体。这些部门全部整并到资本主义体系,显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然而,促成农业商品化的因素很多,我们不可能全面性的检查,特别是在整个社会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绝非可以螳臂挡车的。但是,这并意谓着我们就干脆全面性弃守,不思其后果和寻找其他可能的替代出路。至少可以思考「相对进步」的方式,可以尝试松动这个稳固的结构。我们的目的不必狂妄「务虚」的说要推翻庞大的资本主义结构,一点一点小小的进步,才是务实之道。
因此,与其好高骛远地谈论农业去商品化,还不如先找到解开农民困在商业市场的钥匙。在我们看来,农民陷入困局的原因,无非在于他们在市场上没有足以抗衡的对抗权能(bargain power),为什么没有?因为原本依各地环境差异、依赖农民技术含量不同决定产量的生产过程,程度不一的被资本建构的农技整平了,农民成了没有差异的劳动力相互竞争,农务过程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最后的农产商品。
因为如此,我们尝试找到的一把钥匙,就是赋回农民差异化的能力,让农民有一套自己可以操作的技术和知识背景,可以依自身农地的环境,找到最适的独特方法,种出自己独特风味的水果。我们自己的实验也发现,在部落跟着我们这样操作的两位农民,即便果园是相距不远相同流域的土壤,因为不是依赖外面统一化的肥料和农药,他们种植出来甜柿,含水量和口感就有明显差别。重点是,当我们赋予他们一套科学实验的态度和方法论时,他们就能学会自己观察,调整自己的果园,找到最适合他们果园生态环境的独特风味。一旦如此,他们在市场上就不再只是云云友善环境水果之一,而是独特的,他可以说出一套差异的农作成果。
寻找新的出路:建构新业态
当然,找到钥匙只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建构一个新的业态!正如我们将自己定位为解决农食正义问题的社会企业一般(详见好食机公司理念),如果说,我们不能创新业态,建构一个不同于农食过度商品化市场的新市场机制,那么,充其量,我们就只能是右手赚钱,左手做公益的罗宾翰经济模式(当然这也很是重要的一部份)。因此,我们思考的是,一方面如何更加完善建立起生产者充分以共生方式运用周遭环境资源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则是建构一个让消费者不只是消费农产品,而是「消费整个农作过程」的市场机制。当然,这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同时透过农食教育建构新的消费概念,形成与现今不同的农食「市场」,那么,恐怕也途劳无功。因此,对我们来说,「友善环境」、「适当科技」、「农食教育」是追求农食正义无法分割的三位一体革命。这也是我和小君创办好食机农食整合公司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