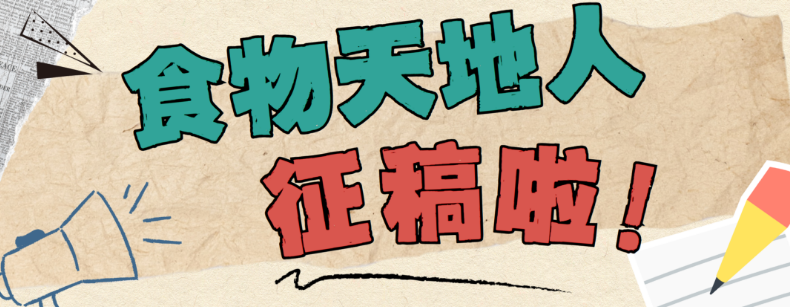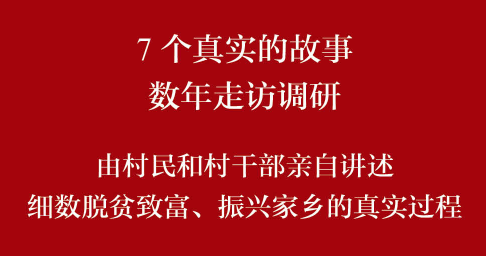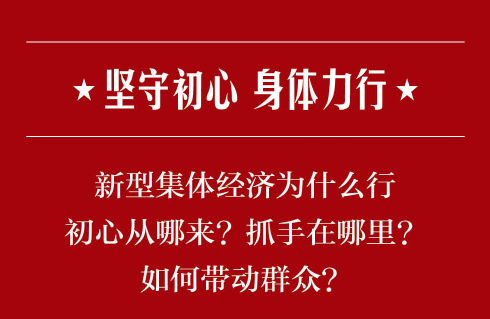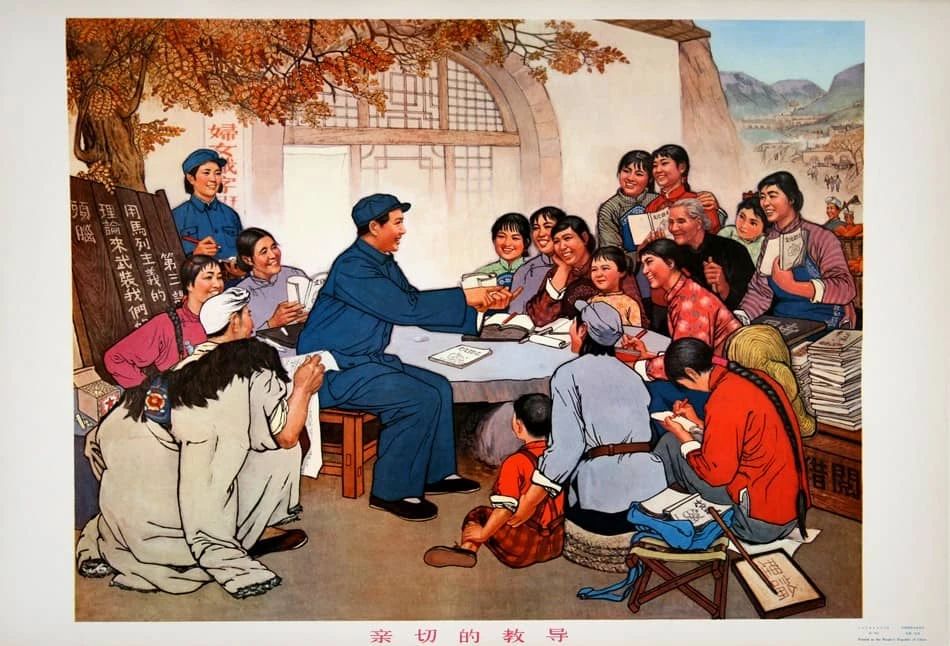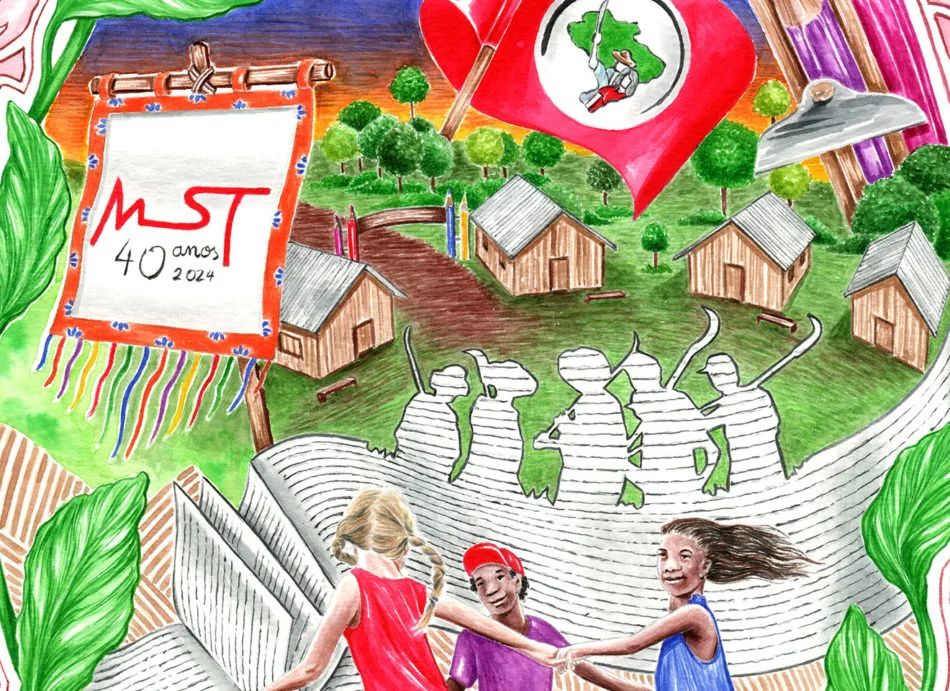台风频发之际,如何打开农村应对气候变化的想象力?
来源: 深耕田野 发布时间:2025-10-08 阅读:501 次
导 语
从“桦加沙”到“麦德姆”,近日华南地区强台风扎堆来袭,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这并非新鲜现象,去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2024年秋季全国气候特征及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即指出“秋台风活动异常频繁,强度大、影响重”。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及各行各业对其关注的增加,各类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地见诸报端,似乎也已逐渐失去其警示意义:每年都有极端天气,但好像每年也都这样过去了,“反常”正在变得寻常。然而,在农村,这些气象灾害不会这么轻易过去。
广西刚走出4月的大旱,又在7月的强降雨中爆发山洪。当蔗农因灌溉成本过高而放弃种地出门打工,当老农花费半生积蓄建起的房屋在旦夕之间被冲垮,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次极端天气事件,这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一个村落命运的转折。但恰恰因此,在农村反而更有可能开展自下而上的、现实的行动,因为对农村而言,气候变化不是一个抽象的科学术语,而是如何自救、寻找出路的迫切挑战。
2025年8月上旬,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深耕”,详细介绍附在文末)在从化村里组织了一场工作坊,讨论农村应对气候变化的话题,总结过去四年的探索经验。作者指出,站在农村的立场去看待气候变化,就要求我们看到其中的复杂性,在“发展的脉络”中展开讨论:不论是气候变化的成因还是它所造成的结果,都远远超出纯粹自然科学的范畴,而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通过将政治经济分析同在地实践紧密结合,深耕对农村应对气候变化之路进行了更为深刻、全面的思考与诊断。在本文中,作者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气候变化影响农村的三重意涵,并呼吁在田野里摸索地方化的方案。从“生态-生计-文化”的地方系统出发,本文超越了农村在气候灾害中“等待救援/补助”的受害者叙事,展现了地方主体性、能动性的一面,为我们理解农村发展、推进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想象力。
作者|深耕人
责编|知为、曳葭
后台排版|童话
一、作为发展问题的气候变化
深耕过去几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实践,在资源和话语方面,都得到了先行伙伴的支持。用气候变化议题的话语来说,是经历了从减缓到适应、从风险应对到韧性社区建设的转变,目前也还在持续探索的过程中。支持过深耕的伙伴包括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万科公益基金会、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合一绿)、爱德基金会等。
其中,合一绿的李大君作为跨越环保与社区发展领域的资深工作者,对深耕理解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帮助。2023年,也是在大君主持的“恒星伙伴计划”的支持下,深耕在村里召集了第一次关于气候变化的交流,希望推动的主题是“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奔赴”,想要把气候变化的议题放回到发展的脉络中理解。就此而言,2025年8月的工作坊是对2023年交流会的延续。
那么,为什么要在发展的脉络中讨论气候变化?这里既有专家和资深人士的见解,也有深耕在实践中的切身体会。
2010年,丁仲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讨论到“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有一个鲜明的立场,是将碳排放权与国家的发展权关联起来。因为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多发展就意味着高能耗、多排放,减少碳排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发展的限制。丁仲礼院士当时立足于中国的发展需求而作出的解释,或许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次科普,将气候变化的处理方案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利益、以及某种意义上的个人利益关联起来理解。而国家2020年提出的“双碳”目标,也同样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作出根本性的转变。
2023年3月,在恒星伙伴计划与深耕共同召集的交流会上,大君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的困局(点击阅读:气候变化,从“国际话语”到“本土表达”),延续了“将气候变化当作发展问题”的基本立场,并借用公益前辈的话指出: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一定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换言之,要真正应对气候变化,就一定要以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反思为基础。
这是因为,气候的异常变化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后果,是人类社会工业化的碳排放所造成的;反过来,气候变化也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继续运转下去的紧箍咒,是现阶段必须权衡、超出临界值就会摧毁发展成果的重大风险;而在某些情况下,气候变化还可以包装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气候变化并不是外在于发展的孤立问题,而是发展的一部分,深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看似巧合、实则必然的是,气候变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一致的体验:它们无差别地笼罩了所有人、使任何人都不可抗拒和逃避;但不同的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会完全不一样、甚至会走向根本的对立。回看气候变暖的历史轨迹和国际谈判的博弈与起伏,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系统的变革作为基础,那么,气候变化引发的后果和应对的责任,不仅在国家之间是不平等分布的,也会极不对等地落到一国之内的城乡居民头上。
深耕团队长期在农村工作,也对此深有感触。农业本来就是靠天吃饭、在极端天气下产量越来越不稳定,又加上市场的挑战,所以极易走向破产;农村老人面对极端天气的恐惧和无奈,根本也是因为村庄年轻人外流和老人独自留守才成为严重的问题。而农产品市场不稳定、年轻人的外流等,则要归因于城乡之间的结构性不公正。
在目前的发展战略和政经结构中,农村既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土地和原料,也以农民的肉身承受了城市化的不当后果。所以,在农村,气候变化的影响看起来是自然结果,但无一不是在现代化进程已使得农村破败的状况下发生的。从发展权的角度来理解气候变化,当年丁仲礼院士面对记者的挑战性提问,曾反问:中国人就不是人吗?那么,在城乡不公平的情境中,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农村人就不是人吗?问题不在于气候变化,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政经系统如何变化。
所以,既是得益于专业人士的启发,也是从自身的实践中深有感触,让深耕更坚定,不能将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单独的问题来理解。气候变化对农村有什么影响?影响发生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气候变化对农村发展的启发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回到农村发展的脉络中来讨论。
二、气候变化影响农村的三重意涵
当我们把气候变化放回到农村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就需要看到:
(1)气候变化和农村都是很大的概念,我们需要跳出概化论述,在具体的农村情境中理解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
(2)社会发展在农村的后果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当气候这个变量发生变化、并作用于农村的系统时,它的作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
(3)生态是农村的基础,而气候是生态的构成要素之一,气候的变化即生态的变化,它会对农村的发展路径提出挑战,特别是如何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
概括来说,这三个方面分别涉及到:具体的影响、影响的机制、生态的视角。以下更具体地讨论。
1.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村的影响全面而复杂,如果笼统地讨论,就显得大而无当、模糊取巧。但现实中,确实有很多讨论稍显“偷懒”,比如,未做仔细分析、就将很多问题归因于气候变化。
其实很多研究已经指出,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不同农作物的影响并不相同,在大部分农村的农业饱受极端天气威胁时,某些区域甚至有可能受益于气候变暖、而产生新的农业发展机会。中国农村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差异,使得我们讨论气候变化对农村的影响时,必须说清楚:什么地方的什么农村,因当地局部气候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本来就“十里不同天”的山区,更需要具体结合当地的条件来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深耕工作所在的从化北部片区,当深耕开始有意识地理解本地的气候条件后,才更看到,位于从珠三角平原向粤北山区过渡地带的这一片区域,本来就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更因地势向北抬升、拦截大量水汽,使得本地的降雨特别集中。而从化北片山区又是丘陵地带,其间布满山区性河流,也就使得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及相应的次生灾害。关键是,这个区域内的村庄和农田都是位于河谷地带,与水同在。因此,洪涝灾害是本地最突出的气候风险,历史上也曾给本地的村庄造成过不同程度的危害,每年总有大大小小的影响。此外,偶发的持续干旱、倒春寒等,也会对农业有很大的影响,但这又要结合到具体的作物来看。倒春寒会导致当地的青梅减产,因为青梅正是在3-5月挂果;持续的干旱往往在秋冬季,对当地种植较多的红薯则非常不利。对于本地村民来说,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因此,村民其实对于极端天气是有非常直接的感受的。如何在极端天气下让农业的产量稳定,以及,当收成变得不稳定、如何降低农业的投入和成本,这两项都是村民非常关心的。
除了农业的角度,还有人的角度。当农村的常住人口以老人为主,气候变化对农民的影响就需要更具体地落到老人的角度来理解。在从化北部山区的村庄,常住人口只有户籍人口的20%多,其中70%是老人。老人的起居和活动环境如何被气候影响,老人在突发灾害时的应对和撤离有什么困难,老人本身脆弱的躯体如何被极端的天气带动“共振”,这些都是要具体考察的。
所以,即使是在从化北部山区这样一个小区域,要弄清楚气候变化对村庄有何具体影响,也并不容易。
2.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
如果要设计农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还需要弄清楚,当一个变量(气候)在农村的系统中变化时,它如何起作用?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如何产生后续的效应,让我们不得不将农村应对气候变化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来对待?这依然要回到具体农村的具体情境中去考察。
前面提到,气候变化对农村的影响,是在现代化进程已使得农村破败的状况下发生的。我们有一种整体的认知是,当农村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规划中没有出路时,农村普遍空心化、老龄化,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基层治理涣散,气候变化对农村的影响就会被放大。但这也还是一种普遍的道理。气候作为一个变量所牵动的农村变化或影响,在以农村发展的系统性困境中,其作用机制不仅仅是放大,可能还会组合不同的条件形成因果关联。这些要进入当地村庄的细节的时候才更清晰。
比如,农村青年外流后,农田就可能抛荒、或者水田改旱地(因为水稻太费人工、老人做不了),农田水利设施没人维护,那些仍然在村里做着小规模农业的老人,在面对持续干旱的时候就会更被动。又比如,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洪涝灾害,虽然政府和村两委都有完善的减防灾机制,但村里只有老人、平时连应急演练都很难做全,导致减防灾机制无法顺利落地和运作,实际上也就增加了洪涝灾害的风险。
深耕团队对于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因为理解到这一层之后,才能说清楚气候变化与从化北部山区各村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在村里做气候变化的工作才有了那么一点点实感。之前总是觉得很虚。
在2023年交流会时,深耕还在反思,为什么在村里推动碳减排和气候变化的减缓工作这么难(点击阅读:如何跟村民谈气候变化?深耕已经填了好几个深坑)。尽管当时在村里的工作很难,但回头来看,那一段经历对于深耕团队在农村情境中理解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要做碳减排和气候变化的减缓工作,深耕就直接进入到了本地农业的处境中,尝试梳理本地常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情况,并用推动农业生态转型的方式来实现减排。但是,尽管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真的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村民对此也有很直接、强烈的体感,但大家并不会因此而转向生态农业。而且,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因为对于农业的定位和期待不一样,在调整农业的种植方式上的动力也完全不同。总体来说,大家更加在意能不能有稳定的市场和价格,没有这个配套的条件,生态转型就推不动。
我们理解到,农业的困境是无法直接归因到气候变化的——相较于市场风险而言,气候变化对农业产业的影响还是其次,农业的出路更不是做一些气候变化视角的工作就能走出来的。农业面临的依然是老问题和系统问题,是发展脉络中的问题,需要做的是构建多层次的生态产业链。当然,稳产量、降成本也是可行的切入点,但同样也受到市场条件的影响,而且,也与农业的规模(面积)、性质(主粮/蔬菜/水果等)、农民的年龄(回报期待/劳动力条件等)等因素高度相关。
同样,我们看到,从化北部山区的农村老人面临着行动/出行的安全风险,因为本地的高温高湿气候导致很多路面长满青苔。其实这对年轻人来说就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老年人易摔倒、一摔就会长期倒下的状况,让路面青苔及其背后的气候条件成为一个问题,而农村的常住人口就是老人,所以青苔就变成了一个公共问题。要识别这个问题及其发生的机制,需要的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视角,更需要老人视角。
所以,气候变化对农村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需要多角度的视野才能理解的,也需要足够深入、长期的观察才能捕捉到。这也是我们特别强调要把气候变化放回到农村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的原因。
3.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视角
目前讨论农村应对气候变化时,很常见的做法是从风险和需求的角度切入,从识别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开始、设计对应的行动。这很现实,因为气候的变化搅动了农村的条件、产生了问题,所以需要做针对性的回应。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或启示还不止于此。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议题提出来,是因为它挑战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即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在农村,这样的挑战更直接,因为大大小小的村庄本身就是在对地方性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和互动中发展起来的。村庄有多少土地、适合种什么,山林里又有什么可利用的、如何利用,村民用的水从哪里来、丰水/枯水期有什么特点……村庄的生产生活,无一不是以地方生态为基础,进而形成“生态-生计-文化”的地方系统;而村庄发展的空间,也受到生态的硬性制约。地方生态的构成元素之一,就是地方性气候。
那么,当气候开始变化,对村庄来说意味着什么?气候变化会影响地方的物种分布,并从根本上塑造地方的农业和自然资源吗?气候变化会让某些问题变得更加急迫、上升为村庄的公共问题、并逼迫村庄形成新的运作机制吗……虽然气候变化并不是瞬间发生,这些涉及到农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不会马上就浮现,但也确实要做长远打算了。在气候变化的话语里,这些问题可以理解成“气候变化的适应”或“气候韧性的建设”;放回农村发展的脉络,则是如何重构村庄的“生态-生计-文化”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一定也是社区发展工作。
而从气候变化切入对生态的理解,提出的则如何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无论是整个人类社会,还是某个具体的村庄,都需要思考,人与生态的关系到底要怎么理解和对待。国际的博弈不休、让人感到无力,但在农村,反而有可能开展更现实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自下而上的行动可能是更有希望的。它不一定要朝向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而是回到农村的生存和发展的立场,来看一个具体村庄的人们在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危机下,如何自救、找出路。当一个村庄行动起来、在重建人与生态的关系的过程中成就一个韧性社区,那么,它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它也可以成为更多人来重新理解人与生态的关系的小小场域,具体、生动、真实、有希望。
这几年,深耕在从化北部山区的5个村庄,贴合村民的实际处境和需求,以社区经济、互助养老、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切入,既是在回应实际的问题,也是在回应问题的过程中探索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如何发展。
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具体的挑战,也是探索村庄发展道路的契机。从气候变化进入,深耕团队更加理解村庄和村民的处境,更看到气候变化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农村困境一体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需求回应和风险解决导向,而是重构新的发展方式。甚至,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切入,深耕也期待将村庄发展的过程变成更多人来体验、想象和共创新的发展道路的过程。
三、在田野里摸索地方化的方案
在从化北部山区工作的时候,深耕也注意到,农业发展、养老、气候变化等问题,已经不只是单个村庄的问题,而是整个片区的共同挑战;同样,片区内的农业结构、村民关系、气候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也是一体的。所以,生态产业链辐射多个村庄,互助养老形成片区效应和跨村网络,气候韧性社区建设扩展为气候韧性镇街建设——深耕的工作正从一个村走向一个片区。(点击阅读:广东从化:气候危机下的风险乡村与韧性重建)
但深耕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模式。我们只是以在地化的观察和分析与基础,探索本地的方案。从实践出发,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是重要的:具体地分析气候变化对具体农村的影响,长期、深入地理解气候变化影响当地村庄的发生机制(特别是放回到农村所处的社会发展系统及其后果中来分析),探索地方化的回应方案。
我们认为,要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发生的机制,需要有来自当地的、一线的(田野)调查/观察和分析,更需要有长期投入在农村工作一线的团队。而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对农村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的讨论、关于地方化的应对/地区发展方案的探索,都是稀缺的。因此,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创造更多的条件,来支持和促成这样的观察、分析和行动的发生。因为正是在这样地方化的一线行动中,我们才能看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
这也是深耕在2025年8月组织“农村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坊”的初衷。
深耕简介
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耕)是由一群关心“三农”处境和城乡发展的资深公益人成立的社会服务机构,以“人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为愿景,配合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既在广东本地开展一线社区工作、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域,也协同华南区域的农村发展工作伙伴开展相关实践、推动行业发展。深耕期待成华南区域农村发展领域的枢纽型组织。
详细介绍可点击标题《深耕简介》了解。
图文来源:公众号“深耕田野”
原文标题:系统变化,还是气候变化?关于农村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