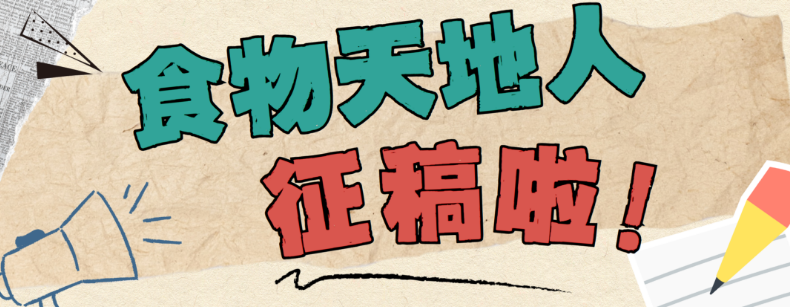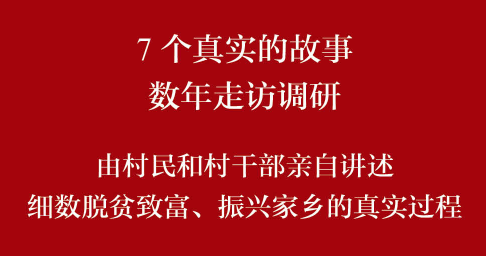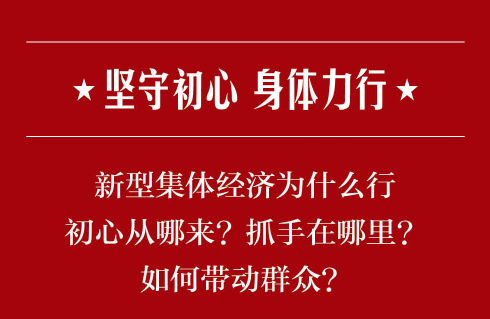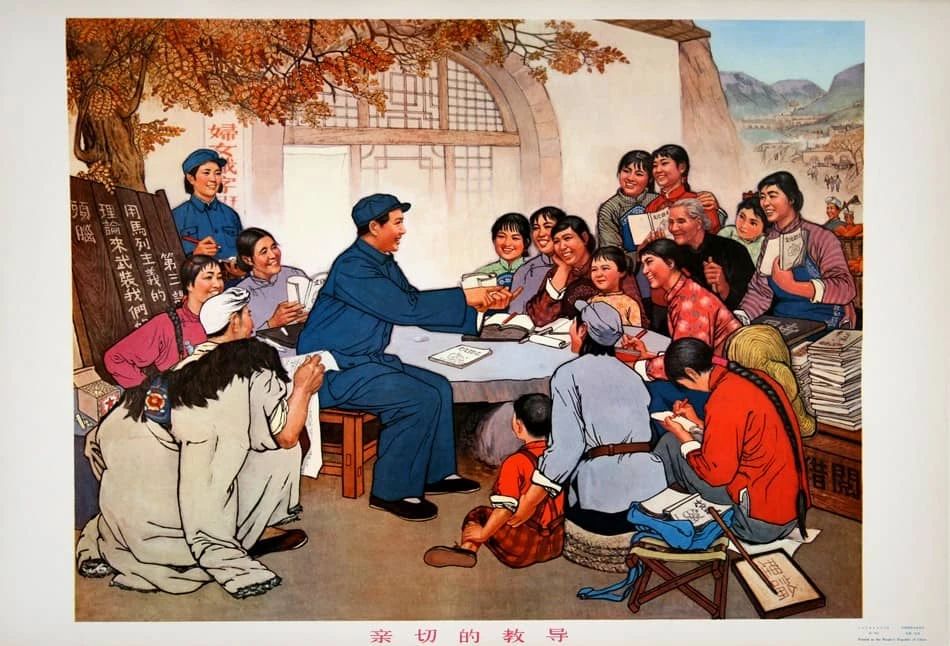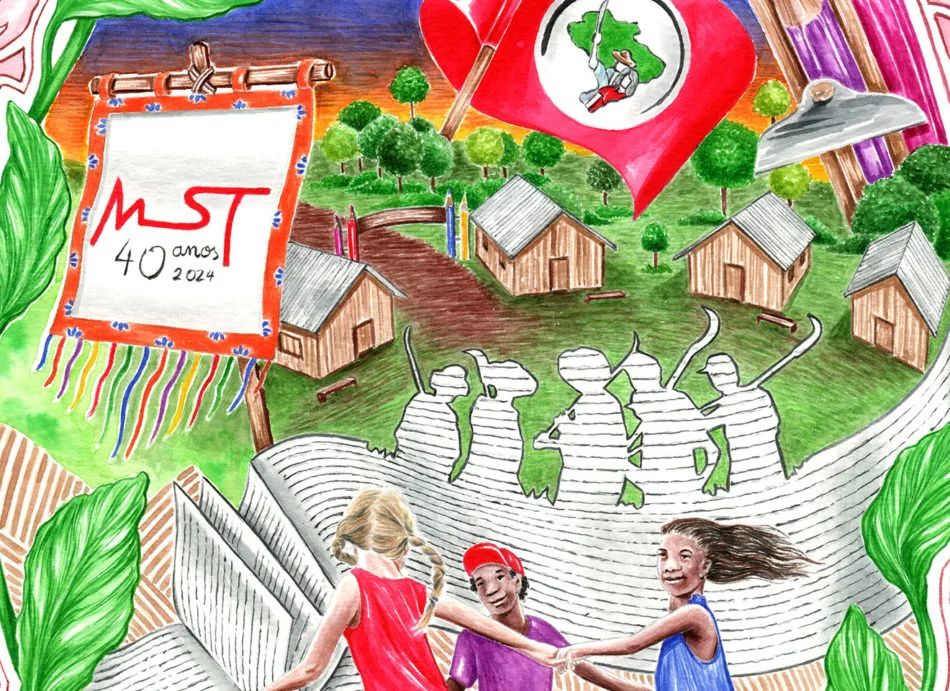转基因风险重重:安全性难料 抗虫效果存疑
来源: 21世纪网 发布时间:2014-07-23 阅读:2180 次
21世纪网讯 或许人们并不了解转基因的具体定义,然而,当这三个字牵涉到人们生活中所吃的“每一口饭”的时候,便自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根据21世纪网此前的报道,2012年绿色和平在购买的76份样品中查出9份转基因检测呈现阳性,其中就包括南方食品的南方纯豆粉(详见《南方食品豆粉被爆含转基因政策滞后知情权受阻》);另一方面,我国的转基因研究面临着国外的专利陷阱,一旦商业化便需要巨额使用费(详见《转基因240亿经费或打水漂非法稻米上餐桌》)。
转基因到底风险几何?种植转基因作物是否真的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在各种争论中,隐藏在转基因背后的“问号”却并没有转换成“句号”,相反,关于转基因的疑问呈现着日益增多的趋势。
尽管支持转基因的人认为所有食品都不可能绝对安全,但是,转基因对活体生物造成癌症、肝肾功能受损等消息的不断传出,牵动着人们的神经。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甚至警告“人民不是小白鼠”。
更为重要的是,转基因一直由于抗虫性以及可以节省农药而受推崇,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其抗虫效果不过是短暂的“过眼云烟”而已。不仅如此,转基因作物还有可能通过花粉传授造成其他植物的基因污染。
在种种的风险面前,人们不禁怀疑,种植转基因作物是否是“丢了西瓜拣芝麻”?
转基因:天使还是魔鬼?
关于转基因是否安全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双方似乎都各有理据。
支持转基因的人认为,任何食品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要保证转基因食品的绝对安全,既缺乏科学依据,也难以实现。因此,只要判定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是实质性相同的,那它就是安全的。而只要在“外观、味道、营养成分、化学结构”方面相同,那就是“实质性相同”。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基因大米和传统大米是“实质性相同”的。
对上述观点,反对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真是“实质性相同”,为什么转基因作物“浑身上下”都是专利?转基因生物发明人在向专利局申请专利时,必须证明这个转基因生物是“全新的、创造性”的,又怎能“实质性相同”呢?
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活体动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证据层出不穷。
此前有国内媒体报道称:俄罗斯科学家在小白鼠交配前两周以及在它怀孕期间,喂食经过遗传基因改良的大豆,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40%%生长发育也非常迟缓,它们的身体都比那些没有喂食经过遗传基因改良的大豆的小白鼠所生下来的幼崽小。同时发现,喂食含有基因食品的母鼠和幼鼠攻击性和焦虑症状增高,而且有些母鼠不再有母性本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转基因食品:天使还是魔鬼?》一书举例称:1997年,一位德国农民开始给自己的奶牛喂食转基因玉米,这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一开始就详细记录喂养、产奶等各种数据,为转基因动物饲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开始三年,这位农民少量喂食了转基因玉米,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第四年当他增加了转基因玉米喂食量,并期待他的奶牛提高产量时,他的奶牛却纷纷出现腹泻、便血、停止产奶等问题,最终,他的70头牛几乎全死光。
2007年3月,法国生物学家塞拉里尼在美国《环境污染与毒理学文献》杂志上发表论文说,雌性试验鼠在食用转基因玉米后开始变胖,而且肝功能受损;雄性试验鼠食用这种转基因玉米后开始消瘦,并伴有肾功能受损。
面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争议,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是“要慎重的”。“他们赞成转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样吗?他们有人类食用转基因的实验结果吗?”
袁隆平坦言,“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这样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他说,“我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但是问题是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转基因对性能力和遗传性的影响是需要实验证明的,如果有年轻人自愿做实验,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那才安全。”
抗虫效果存疑
除安全性外,人们对于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抗虫效果也有质疑。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经理助理俞江丽告诉21世纪网:“目前转基因特征主要有三种,一是转抗虫基因,二是转抗除草剂基因,还有就是同时转抗上述两种的,这被认为是节省农药的使用并且可以提高产量。但从种植的实际情况上看,一开始这些作物的抗虫性还可以,但过了几年之后,次生虫害增加,抗药性增加,相应农药也还是需要大量使用,代价还是很高的。”
1997年,中国从美国孟山都公司引进第一代“转基因抗虫棉”。在刚引进的几个年头,转基因棉花农药使用量、种植成本有所下降,单位亩产总量上升。这些优势引来了媒体和农学家的一致盛赞。
然而,好景不长,转基因棉表现“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一方面,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对纺织机器产生了影响,纤维质量不如常规棉;转基因棉衣分率(籽棉向皮棉的转化率)下降到34%左右,低于常规棉;另一方面,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小虫成大灾”,用药量反而猛增。
对此,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表示,在农业生产上,必须尊重物种生存权,恢复生态平衡。对于“害”虫控制,不能将目光仅盯着化学防治上,或转基因技术上,还要考虑物理、生物甚至人类传统知识的贡献。不能像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继续干那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傻事。
或有基因污染
一个转基因生物在从实验室被释放到大自然中以后,会像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木马一样,因其所具有的优势基因,对其他物种造成侵略,最终导致其他物种灭绝的过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沈孝宙在自己所著的《转基因之争》中写道。
据了解,转基因作物中含有从不相关的物种转入的外源基因,例如,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含有矮牵牛的抗除草剂基因。这些外源基因有可能通过花粉传授等途径扩散到其他物种,生物学家将这种过程称为“基因漂流”。环保主义者则使用“基因污染”的概念:外源基因扩散到其他物种,造成了自然界基因库的混杂或污染。
与其他形式的环境污染不同,植物和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能使基因污染成为一种蔓延性的灾难,而更为可怕的是,基因污染是不可逆转的。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已经悄然发生。
在英国,小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试验地周围,就发现了体内含有转基因蛋白污染的蜜蜂。美国转基因草莓种植地周围50米的野生草莓已经有50%含有转基因,转基因向日葵附近的野生同类25%—38%含有转基因。
1995年,加拿大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油菜,但在随后的几年里,麻烦出现了。一方面,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飘移到附近的杂草,杂草也变得具有了抗性,变成了除草剂无能为力的“超级杂草”;另一方面,收获时散落的油菜籽第二年重新萌发,但如果第二年这片田里种植的不再是油菜而是别的作物,那些萌发出的油菜也将成为“超级杂草”。这些“超级杂草”还会通过交叉授粉等方式,污染别的植物。这就是著名的加拿大“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事件。
在中国,这样的风险并非没有。
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表示:前几年曾经在湖北进行过转基因水稻的实验性种植,当时管理没有跟上,像转基因种子就没有限制,什么人都可以买到。其担心,转基因水稻也许会出现在不适合种植的地方,污染当地农作物。(21世纪网 戴闰秒 陆晓辉 dairm@21cbh.com luxh@21cb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