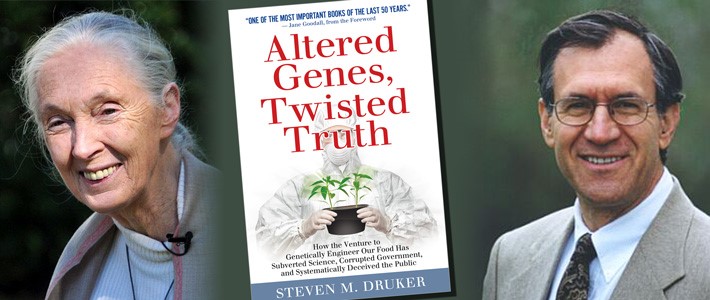科学的政治化:美国挺转派与反转派科学家的斗争始末
基因工程(术语是“DNA重组技术”,也被称为“生物工程”和“基因剪接”)包含一整套强大的新工序,它可通过转移、剪接来重组DNA片断,来实现以往不可能做到的基因组重组。这样的话,基因工程可以产生相当多样的产品。它可以拷贝并导入生物体同源的部分基因,改变一些基因序列,重新设置开启或关闭基因的功能,或者将不同的或远缘的物种基因移植到个体中。更厉害的是,基因工程可以改造任何一种生物体,不管它是细菌,植物还是动物。每一次改造都会产生一系列独特的后果(包括意料之中的也包括意料之外的),具体后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生物体的种类,所采用的转基因技术、转基因在DNA分子中的位置以及生物体生存的环境等等。
挺转的科学家断然肯定基因剪接技术是安全的,但恩斯特·迈尔和菲利普·雷格尔两位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对基因技术的风险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基因工程从根本上改造了复杂的生物体,它们有的长在农田里,有的与自然界更丰富的物种共生,那些专业仅限在生物领域的人怎么能如此确定转基因一定是安全有效的呢?转基因如何适应生态系统,是否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干扰,对于这两个问题,转基因支持者们没有拿出科学证据做评估。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分子生物学家的行业声明视为权威,甚至连政府的政策也受到它们强有力的影响。
以下是两派科学家关于重组DNA研究的不同立场以及双方角力的过程。
角力第一阶段:势均力敌
1970年:科学家发现了DNA分子可以被准确剪接的方法,几年后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细菌。
1973年6月:出于对转基因技术的巨大威力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恐惧,科学家团体内部发起了一次对话,并将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两封公开信,反映出基因工程确实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人们对此感到担忧是合理的。这种情况是史无前例的:一群科学家自发地限制自己的研究,并呼吁他们的同行也这样做。
1974年10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最后命名为重组DNA顾问委员会[RAC]),该小组在随后很多年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5年2月:有一百多名研究者参加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的艾斯洛马会议中心举办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最后达成共识,设立了一系列安全规范,包括只能研究那些无法在实验室以外存活的孱弱细菌。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针对重组DNA研究制定的规范公布了,它对所有接受NIH基金的组织都设立了限制,它禁止科学家蓄意将任何带有重组DNA的生物释放到环境中去。
由于要求对重组DNA研究施行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担心他们的研究将会落后于其它国家的科学家,从而导致美国失去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此外,受简化论信念的灌输,使得他们认为这一新科学将通过精确的基因和化学操纵来解决人类世界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人类的智慧可以完全掌控这个过程,而意外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对生物科技充满信心而没有考虑风险,也没有为其他负面的影响做准备。于是,许多科学家公开放弃或否认先前采取的谨慎立场,转而肯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和该领域的科学性。
在这一阶段,对重组DNA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派要求减少政府监管,放开研究;一派认为应该谨慎对待转基因,政府应该更大程度地介入,这两派关于基因工程的争论,势力基本势均力敌,达到一个平衡点。总的来讲对基因技术的担忧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联邦政府的监管还没有放松。
角力第二阶段:玩弄科学、捣破监管
1977年:平衡被打破,天平开始倒向生物技术科学家的那一边。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重要新证据的出现。关于新证据的关键消息是从三个会议中传出来的。这些会议的目的是评估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第一个会议于1976年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召开,第二个会议于第二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尔茅斯举行,第三个会议是1978年在英国阿斯科特召开的)。三个会议共同传达的信息给人这样的印象:目前,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转基因是安全的,并且专家们对此已不再有任何担忧了。然而,这样的印象其实是被误导的。
误导手段包括:筛选参会人员、操纵议题,公布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而且首要任务是讨论如何说服公众。会议的组委会主席戈尔巴奇在会后写了一封报告总结会议结果,这项结果(危险基本上不存在)不仅被媒体和公众接受,还迅速在科学界获得地位,得到著名生物学家的推崇,美国国家科学院(NAS)进一步歪曲事实,声称证据显示,在一般情况下,基因工程的风险无足轻重。
这之后,打着证据显示研究安全的旗号,分子生物学阵营中的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成员串通一气,共同发起了一项庞大的游说行动,目的是阻碍监管的实施,并最终达成目标,显示出生物医学研究人员能获得权力以左右政府监管,它还证明了这种权力可以通过宣传推销式的措辞来获得,尽管这些措辞既毫无依据又严重可疑,只要声称是基于科学的就可以了。
1978年4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表声明,提出证据提供者应该转变(由技术支持者转到管制支持者身上),此项决定影响到之后所有关于转基因生物的政策。这几次会议给科学家和大众带来虚假的印象,使他们认为重组DNA技术总体上是安全的。而一些生物学家的警告等负面结果无一被宣传。于是,国会和美国人民被误导而相信研究结果全面支持对转基因的放松监管。这项争议的发展历程揭示出:科学研究者坚持以研究自由为重,而公众的需要、公共安全和科学精神被放在次要的考虑。
在公关方面,一位科学家主张使用大肠杆菌K-12,他提出K-12的危害性极小,因此,这项研究将会得到很多正面的公众支持。说明,大部分人倾向于避开那些可能会产生令人难堪的危险的实验,而选择那些可以提升正面效应的实验——追求令人满意的结果,而牺牲最优的科学价值。
角力第三阶段:生物技术势力的扩张,质疑声音渐起
到了新阶段,基因工程技术从医学领域扩张到农业领域,从业者开始反对环境释放禁令。为了打消公众对于转基因的再度恐慌,分子生物学家一口咬定,转基因农作物非常安全,就像无法在实验室外生存的转基因细菌一样安全。
1981年4月,一些有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发起了一项倡议,意图取消转基因的所有强制性管制措施,这与政府内部日益抬头的反监管的呼声遥相呼应。“分子生物学家已经成为企业家了,而不仅是单纯的行业顾问,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把个人财富和事业的成功投注在了生物技术的牟利之上。”
最终,环境释放禁令取消,1980年6月,重组DNA顾问委员会批准了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农田试验。而当时,根据1983年国会候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没有其他机构或者部门同时拥有专业知识和权力来对各类转基因物种的环境释放影响进行合理地评估。”该报告还特别指出,美国环保署的相关能力为“未知”,美国农业部的经验为“有限”,而RAC的专业能力“不足”。报告还提到,美国农业部表现出“不愿意参与该领域的监管。”
1983年,恩斯特·迈尔和菲利普·雷格尔下定决心要用真正的科学予以还击,以坚实的科学驳斥转基因普遍安全的论点。
1. 基因剪切并不一定总削弱生物的生存能力,一些改变甚至可能加强物种的竞争力,使其可以在野外繁荣生长,成为主要的有害物种。
2. 与传统育种相比,重组DNA技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组合基因。考虑到这一论点所忽视的事实,这种差异是很明显的。
然而,尽管与事实不一致,转基因生物的普遍安全的论点却往往通行无阻。同时,受其支持者的声誉影响,这些论点被政府和媒体当成权威观点而接受。无论是这些观点,抑或是它所带来的环境安全问题,都没有经过科学界的认真评估。迈尔和雷格尔试图在生物科学界再发动一场对话,分析转基因的生物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在组织研讨会的过程中,他们遇到来自政府、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种种阻碍,越来越了解政治倾向和压力会如何影响科学家对转基因的看法,他们尝试减轻这种影响。
1984年8月,研讨会在纽约州班伯里市中心的冷泉港实验室召开。参会双方都很震惊,雷格尔一方看到有如此多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依据在他们看来是“荒唐的伪科学”观点而宣称所有转基因生物都是安全,他们感到“震惊”。“使他们更为震惊的是”,雷格尔说,“一些政府和业界人士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进行的项目。这些明显有危险的生物体正在被研发出来,大家对此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它们将在短期内释放到环境中。” 反过来,分子生物学家们看到 “他们主张的转基因安全论被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所不齿,而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1985年6月,另一次会议在费城召开。在会议过程中,其他生态学家更详细地展示了其证据,以揭示转基因安全性的漏洞。这次会议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实际作用在于它明确表明生态学家必须参与到生物技术评估方针的制定,也必须参与到对转基因生物的风险评估工作中。这也带来了政府决策的改变。生物技术放松管制的计划要被重新评估,原本要对生态学基础研究削减经费的计划将被取消,并且环境保护局开始更积极地就转基因问题寻求生态学家们的建议。
角力第四阶段:国家权力挺转,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
为了给生物技术产业打开方便之门,里根政府调整了权力结构以限制美国环保署的角色。将转基因生物的环境安全责任交给了美国农业部,而非最具有专业环境知识的机构,因为美国农业部对生物技术态度更友好,并且不愿意让转基因生物受到监管。
1986年6月18日签署的《生物技术管理协调大纲》最值得提出的一点,就是将白宫的指令,“监管最终产品,而不是生产过程”,纳入了这个大纲中。这样,监管的对象就只是作为产品的转基因生物的具体特性,而不是生产它们的方法——这使得转基因生物即便是用重组DNA技术生产出来也不会受特定要求的监管。尽管白宫将这个结果表现为是由科学驱使的,但是很显然其主导的驱使力量是政治。并且,就像十年前美国研究分析公司(RAC)的指南那样,它有力地让公众平静了下来。
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行的一本意见书,以及1989年发布了一篇更为广泛引用的报告,都淡化转基因的负面影响,为促进转基因生物的快速发展而服务。表明政治力量站在支持基因工程的分子生物学家那边。
综上所述,在基因工程建立的头二十年,它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家政策,以至于事实上它的全部议题都被连续两届政府接受,并且得到其热烈的推动——而且这种情况还将会在此后三届政府那儿继续下去。基因工程工作者个人获得了(并且将会继续获得)政府慷慨的资助来进行他们的研究;基因工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拿到许可,在最低限度的监管下开发和部署一系列新产品,尽管很多专家已经得出结论,这些新产品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另外,它对信息的宣传和阐释进行广泛的控制,可以灵活地操纵政府、媒体以及大众(对他们)的印象——把猜想冒充为确凿的证据,有局限的结论变成普遍的事实,同时压制那些威胁他们利益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