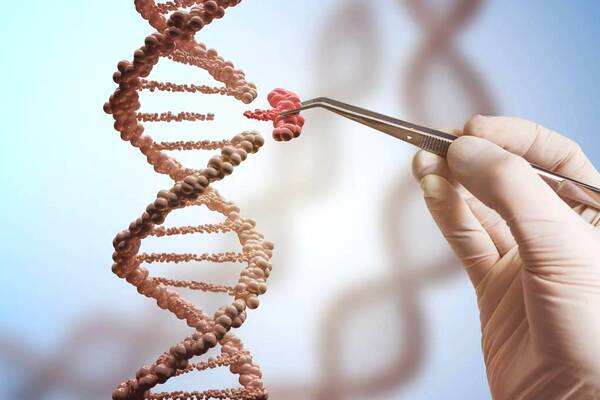基因编辑风险不可控
来源: 《独立科学新闻》 发布时间:2019-10-15 阅读:2812 次
许多人认为,活细胞内的基因编辑是新千年的卓越技术突破。医学和农业研究人员已经迅速将它作为发现细胞和生物功能的技术。但是它的商业前景要复杂得多。
基因编辑有许多潜在的用途。这些包括改变细胞来治疗人类疾病,改变作物和牲畜来繁殖和农业。此外,中国研究人员贺建奎声称,他通过改变一种叫做CCR5的基因,编辑了人类婴儿来抵抗艾滋病毒,这一举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对于大多数商业应用来说,基因编辑的吸引力在于简单和精确:它可以在精确的位置改变基因组,而无需插入外来的DNA。这就是为什么在流行的文章中,基因编辑经常被称为“微调”。
然而,这种扭曲的叙述是一种假设,而不是既定事实。它最近遭受了巨大的冲击。7月下旬,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最初出生于2016年的两只小牛的整个基因组。这些小牛是由生物技术初创公司重组技术用一种叫做TALENS的基因编辑方法编辑。这两只重组动物因基因改变切除了它们的角而成为生物技术名牛。没有角的牛被称为“无角牛”。无角小牛是众所周知的,因为重组学坚持认为它的两只编辑过的动物被极其精确地改变了,只拥有无角的特性。
然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研究人员发现并不精确。重组技术的每头小牛都有两个抗生素抗性基因,以及多余细菌DNA的其他片段。因此,重组学显然不知道,在其编辑位点附近有4000个碱基对的DNA,这些碱基对来自质粒载体,用于引入无角性状所需的DNA。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发现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重组学的无能上。这家初创公司未能找到(或者可能是寻找)自己作为编辑过程的一部分添加的DNA。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发现,巴西终止了一项始于重组动物的育种计划。
但是除了最近关于基因编辑的另一个发现之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发现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令人惊讶的外来DNA可以常规地进入被编辑动物的基因组。这种遗传物质不是故意放在那里的DNA,而是标准编辑程序的污染物。
这些发现没有在科学或大众媒体上报道。但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它们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于基因编辑的商业和监管前景也是如此。它们至少意味着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防止游离的DNA的污染,同时对基因编辑的细胞和基因编辑的生物体进行彻底的检查。正如重组案例所表明的,这些需求是开发人员自己可能无法满足的。
一、了解游离DNA的来源
早在2010年,研究人类细胞的研究人员就表明,一种叫做锌指核酸酶(ZFN)的基因编辑形式可以在编辑目标位点插入外源基因。这种外源基因的来源,就像重组学的小牛一样,是编辑过程中使用的质粒载体。
理解质粒载体的存在需要了解基因编辑的基础知识,令人困惑的是,这与普通英语中“编辑”一词的含义有很大不同。
最终,所有的DNA编辑实际上是由被称为核酸酶的酶切割DNA,这些酶应该只作用于活细胞基因组中选定的位点。这种切割产生双链断裂,切断(因此严重损坏)染色体。研究人员最常用的切割酶是福克ⅰ酶(用于TALENS类型编辑)、卡斯9酶(用于CRISPR)或锌指核酸酶(用于ZFN)。
切割事件后,细胞进行修复。实际上,这种基因修复通常是不准确的,因为大多数细胞的自然修复机制有些随机。结果被称为“编辑”。研究人员通常必须从许多“编辑”中选择一个来获得他们想要的。
像几乎所有的酶一样,这些核酸酶是蛋白质。像大多数蛋白质一样,它们生产起来有些棘手,一旦生产出来就相对不稳定。因此,研究人员通常不会直接生产DNA切割酶,而是将载体质粒引入靶细胞。这些载体质粒是编码所需酶的环状DNA分子。(载体质粒DNA也可以编码CRISPR编辑技术所需的引导核RNA)。实际上,这意味着TALENS、Cas9和其他切割酶最终由靶细胞自身产生。
因此,从研究角度来看,引入DNA比引入蛋白质容易得多,但它也有一个缺点:必须将非宿主(即转基因)DNA引入待编辑的细胞,这种DNA可能最终进入基因组。
质粒载体并不简单。除了指定核酸酶,重组学使用的载体质粒包含抗生素抗性基因,加上lac Z基因,加上每个基因的启动子和终止序列,加上两个细菌复制起点。这些DNA成分中的每一种都来自广泛多样的微生物。
正如奥尔森等人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显示的,使用TALENS和ZFN类型的DNA切割器可以导致质粒载体在靶位点的整合。2015年,日本研究人员显示,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方法对小鼠受精卵进行的基因编辑也容易受到非宿主基因无意插入的影响。
此后,在许多物种中观察到外源基因在目标位点的类似整合:果蝇、青鳉鱼、小鼠、酵母、曲霉菌(真菌)、线虫、大型溞和各种植物。
二、杂散DNA的其他来源
在标准基因编辑方法中,载体质粒本身并不是潜在的外源基因污染的唯一来源。
今年早些时候,同一个日本小组显示,大肠杆菌基因组中的DNA可以整合到目标生物体的基因组中。大肠杆菌的获取被发现相当频繁。长的非预期的DNA序列的插入发生在编辑位点总数的4%,其中21%是来自大肠杆菌基因组的DNA。大肠杆菌DNA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用于生产载体质粒的大肠杆菌细胞。载体质粒,即DNA,被大肠杆菌基因组DNA污染。重要的是,日本研究人员正在使用载体质粒制备的标准方法。
更有趣的是,在同一篇论文中发现,编辑后的小鼠基因组可以获得牛或山羊的基因。这可以追溯到在小鼠细胞的标准培养基中使用胎牛血清;也就是说,体液通常是从奶牛身上提取的。这种血清含有从任何动物物种中提取的DNA,因此在一些实验中插入了山羊DNA(这发生在用山羊血清代替小牛血清的时候)。
更令人担忧的是,插入小鼠基因组的基因序列包括牛和山羊逆转录转座子(跳跃基因)和小鼠逆转录病毒基因(艾滋病毒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因此,基因编辑是有害病原体(包括但不限于病毒)水平基因转移的潜在机制。
用于基因编辑的细胞培养物中也存在其他不需要的DNA的潜在来源。2004年,研究人员观察到,当肝癌细胞系的细胞出现DNA断裂时,其中一些断裂由乙肝病毒序列填补。换句话说,污染胎儿血清的病原体,如DNA病毒,也应该引起关注。
此外,来自其他物种的多余的DNA的插入可能不局限于预期的靶位点。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因编辑酶可以在基因组中不需要的位置起作用。意外引入的DNA也可能最终出现在这样的位点。这已经用CRISPR在人类细胞和植物中得到证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上面提到的更多奇异的DNA也可以在那里整合,但这尚未经过专门测试。
三、编辑细胞中多余DNA的含义
总之,新发现非常简单:无论基因编辑的精确类型如何,在细胞内切割DNA都会使基因组容易获得不需要的DNA。不需要DNA可能来自编辑过的细胞内部,也可能来自培养基,或者可能来自添加到培养基中的任何生物材料,无论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因此,不难想象,例如,基因编辑的动物会成为导致新的或不受欢迎的,病毒或支原体发展和传播的繁殖种群。
纽约医学院的斯图尔特·纽曼(Stuart Newman)是细胞生物学家,负责任遗传学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也是《生物理论》杂志的主编。根据他的说法,来自细胞培养的DNA的添加“在CRISPR和其他基因修饰技术的安全性的讨论中没有被提及”。
纽曼说,如果基因编辑的目的是产生改变的生物体,细胞培养基“含有基因,如果通过CRISPR/Cas9以额外的数量和不受控制的染色体位点重新整合到合子基因组中,可能会导致发育问题”。
“我毫不怀疑大肠杆菌的DNA已经无意中被整合到许多CRISPR目标中,它很可能会引起问题,就像在无角的牛身上一样。”
类似的问题也适用于人类应用。研究者贺建奎的基因编辑的人类婴儿并没有公开提出其他物种的基因整合。显然,应该是这样。例如,贺建奎从哪种细胞类型中纯化了他可能用来编辑CCR5基因的蛋白质?兔子细胞?昆虫细胞?这些至少是标准方法。
第二个重要结论,也是重组学案例的例证,是研究人员通常不寻找游离的DNA。如果他们去看看,可能会有更多的例子被报道。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上面引用的研究使用了基因编辑的标准方法。唯一不典型的方面是为检测多余DNA付出了额外的努力。
四、基因编辑与转基因生物
这些最近的发现也突出了基因编辑的一个更普遍但很少讨论的方面。尽管基因编辑和基因工程师的目标被认为是非常不同的,但实际上他们的标准方法几乎无法区分。
以农作物为例,它们是基因编辑中最直接的商业利益所在。为了编辑植物,将载体质粒形式的DNA引入植物细胞。与动物基因编辑方法相反,这种载体质粒是必需的(而不是可选的),因为蛋白质不能穿透植物细胞壁。这种载体质粒必须进入细胞内部,这需要基因枪或被DNA转移细菌根癌农杆菌感染。最后,体外细胞培养用于将编辑后的细胞再生为完整植物。
基因枪、组织培养和根癌农杆菌都是农作物的标准基因工程方法。它们也都会产生突变。也就是说,它们会破坏基因。根据所用方法的具体情况,例如组织培养的时间长度,总的结果可能是每个基因组有一万个突变。对于作物的基因编辑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目标上的突变可能会比成千上万个非目标上的突变相形见拙。
与转基因生物的另一个必要的比较是,在商业化很久之后,它们的基因组中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外来基因。康奈尔大学的抗病毒木瓜在夏威夷上市,结果发现含有至少五个(可能是六个)独立的转基因基因片段。康奈尔大学之前告诉监管机构,它的木瓜含有两个转基因品种。独立研究人员发现,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当时生长在美国96%的大豆田里,其外源基因比孟山都声称的要多得多。
因此,如果你只听将基因编辑的“精确的”“调整”与“混乱的”、“随机的”基因工程进行对比的修辞,你很难怀疑,当涉及到植物,通常也涉及到动物时,基因编辑的现实和基因工程的现实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五、是否有多余的DNA的解决方案?
解决多余的DNA(在编辑站点或远离编辑站点)存在的方法有两种基本形式:预防,或检测后去除。
一个明显的预防措施是避免使用载体质粒和未定义的培养基(未定义的培养基是指含有活生物体的液体或提取物的培养基)。另一种方法是明确培育(回交)基因编辑的动物和植物,以去除多余的DNA。第三种方法是对它们的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将其与母体基因组进行比较,如果可以找到未改变的细胞系,只选择未改变的细胞系。
但是,这些补救措施很费力,它们既耗时又昂贵,或者尚未完全开发,或者只对某些物种可用。这些解决方案也抵消了速度和易用性的优势,而速度和易用性通常是编辑的首要原因。
对专业知识和努力的需求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第二个主要问题,那就是行业,而不仅仅是重组学,对自我检查不太感兴趣。远比之前的转基因产业更伟大的是牛仔时代精神:抛开问题,奔向市场。因此,大多数基因编辑公司不愿意分享信息,因此,在实践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公司是如何获得他们的“基因编辑”产品的。
许多国家目前正在制定法规,这些法规将大大有助于确定基因编辑可能带来的任何潜在好处中谁受益谁损失。但无论如何,这些结果为政府积极监督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然而,不仅仅是监管机构需要加强监管。投资者、保险公司、记者,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向活跃在基因编辑领域的科学家和公司提出更多的问题。否则,繁荣很可能会误入歧途。
参考资料:
[1] Ahmad,Niaz Mehbub-ur Rahman,Zahid Mukhtar,Yusuf Zafar,Bob Hong Zhang(2019年)基于CRISPR的植物基因组编辑研究..J.细胞生理学。
[2] Bill,ColinA.和JesseSummers(2004年)基因组DNA双链断裂是肝细胞DNA整合的靶点..PNAS:101(30)11135-11140。
[3] Gutierrez-Triana,Jose Arturo,Tinatini Tavhelidse,Thomas Thumberger,Isabelle Thomas,Beate Wittbrodt,Tanja Kellner,Kerim Anlas,Erika Gingos,Joachim Wittbrodt(2018)5‘修饰长dsDNA供体的高效单拷贝HDR..e Life 2018;7:e 39468。
[4] Thomas B Jacobs,Peter R Lafayette,Robert J Schmitz&Wayne A Parrott(2015)利用CRISPR/Cas9技术对大豆进行靶向基因组修饰..BMC生物技术15:16。
[5] Kim,J.&Jin-Soo Kim(2016年)利用CRISPR基因编辑绕过转基因规则.自然生物技术34:1014-1015。
[6] Kosicki,M,K.Tomberg和A.Bradley(2018)CRISPR-Cas9诱导的双链断裂修复会导致大的缺失和复杂的重排。..自然生物技术36:765-771。
[7] 诺里斯亚历克西斯L.,Stella S.Lee,Kevin J.Greenlees,Daniel A.Tadesse,Mayumi F.Miller,HeatherLombardi(2019年)。DOI:https://doi.org/10.1101/715482
[8] Olsen,P.A.,Gelazauskaite,M.,Randol,M.&Krauss,S.(2010)锌指核酸酶介导的非合法基因组整合分析:对靶基因校正特异性的影响.BMC Mol Biol 11,35。
[9] Latham,Jonathan R.,Allison K.Wilson和Ricarda A.Steinbrecher(2006年)植物转化的突变后果。生物医学与生物技术杂志(2006年)7页DOI:10.1155/jbb/2006/25376
[10] Li、中森、刘振斌、邢爱秋、穆恩、杰西卡·科尔霍弗、黄灵霞、提摩太·沃德、伊丽莎白·克利夫顿、卡尔·法尔科、A·马克·齐根(2015)引导RNA引导大豆基因组编辑..植物生理学169:960-970。
[11] 李荣升泉,颜晓芳,苏库马尔·比斯瓦,张大兵,史建新(2017)转基因作物的分子特征:挑战与策略..生物技术进步35:302-309。
[12] 明,R.,S.侯,冯玉峰,Q余,A Dionne-Laporte(2008)转基因热带果树木瓜(Carica Papaya Linnaeus)基因组草稿..自然452:991-996。
[13] 温德尔斯、彼得、伊莎贝尔·塔弗尼耶、安·德皮克、埃里克·范博克斯塔勒和马克·德洛(2001年)抗农达大豆插条的特性研究..欧元食品研究公司Technol.213:107-11。
[14] Ono、Ryuichi、Masayuki Ishii、Yoshitaka Fujihara、Moe Kitazawa、Takako Usami、Tomoko Kaneko-Ishino、Jun Kanno、Masahito Ikawa和Fumitoshi Ishino(2015年)小鼠受精卵反转录转座子序列及反转录剪接mRNA序列的双链断裂修复科学报告5:12281。
[15] 小野龙一、Yukuto Yasuhiko、Ken-ichi Aisaki、Satoshi Kitajima、Jun Kanno&Yang Hirabayashi(2019年)在基因组编辑过程中,外显子介导的水平基因转移发生在双链断裂修复过程中。..通讯生物学2:57https:/www.nature.com/ports/s4200-019-0300-2.pdf。
[16] Wilson、Allison K.、Jonathan R.Latham和Ricarda A.Steinbrecher(2006年)转基因植物的转化诱导突变:分析及生物安全意义.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审查23.1:209-238。